如果你和我一樣對歷史知之甚少,就很難不懷疑現代戰爭作為解決任何問題的功效,除了報應——用一種損害換取另一種損害的“正義”。
戰爭的辯護者會堅持認為戰爭解決了國家自衛的問題。 但懷疑者會問,即使是一場成功的國防戰爭,在生命、金錢、物質、食物、健康和(不可避免的)自由方面的代價,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構成國家失敗。 通過戰爭進行國防總是會導致某種程度的國家失敗。 這種悖論從我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一直伴隨著我們。 捍衛自由的軍事化減少了捍衛者的自由。 戰爭與自由之間存在根本的矛盾。
在現代戰爭中,使用現代武器進行現代規模的戰爭,任何一方都不能將其造成的損害限制在“敵人”身上。 這些戰爭損害了世界。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足夠了解,你不可能在不破壞整個世界的情況下破壞世界的一部分。 現代戰爭不僅使得不可能在不殺死“非戰鬥人員”的情況下殺死“戰鬥人員”,而且還使得不可能在不傷害自己的情況下傷害敵人。
許多人認為現代戰爭越來越不可接受,這從圍繞現代戰爭的宣傳語言中可見一斑。 現代戰爭的特點是為了結束戰爭。 他們是為了和平的名義而戰的。 表面上看,我們製造最可怕的武器是為了維護和確保世界和平。 “我們想要的只是和平,”我們一邊說,一邊不斷增強我們的戰爭能力。
然而,在一個世紀末,我們為結束戰爭而打了兩場戰爭,為防止戰爭和維護和平而打了幾場戰爭,科學技術的進步使戰爭變得更加可怕和難以控制,我們仍然通過政策,不考慮非暴力的國防手段。 我們確實非常重視外交和外交關係,但我們所說的外交總是指以戰爭威脅為後盾的和平最後通牒。 人們總是明白,我們隨時準備殺死那些與我們“和平談判”的人。
我們這個世紀的戰爭、軍國主義和政治恐怖已經產生了真正和平的偉大且成功的倡導者,其中莫罕達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他們取得的巨大成功證明,在暴力之中,存在著對和平的真誠而強烈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證明了做出必要犧牲的意願。 但就我們的政府而言,這些人和他們偉大而真實的成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以和平方式實現和平還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堅持通過戰爭來實現和平這一無望的悖論。
這就是說,我們在公共生活中堅持殘酷的虛偽。 在我們這個世紀,人類對同胞、對自然和文化共同體的暴力行為幾乎普遍存在,虛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對暴力的反對是選擇性的或僅僅是時尚的。 我們中的一些人雖然贊同我們龐大的軍事預算和我們的維和戰爭,但仍然對“家庭暴力”感到痛惜,並認為我們的社會可以通過“槍支管制”來安定。 我們中的一些人反對死刑,但反對墮胎。 我們中的一些人反對墮胎,但主張死刑。
人們不必了解太多或想得太多,就能看到我們所建立的經批准的暴力事業的道德荒謬性。 墮胎作為生育控制被證明是一種“權利”,只有通過否認另一個人的所有權利才能確立這種“權利”,這是戰爭最原始的意圖。 死刑使我們所有人陷入同樣程度的原始好戰,即一種暴力行為會被另一種暴力行為報復。
這些行為的辯護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暴力滋生暴力,這一事實已為世仇歷史所證實,更不用說戰爭歷史了。 為“正義”或確認“權利”或捍衛“和平”而實施的暴力行為並不能結束暴力。 他們準備並證明其繼續下去的理由。
暴力各方最危險的迷信是認為經批准的暴力可以預防或控制未經批准的暴力。 但是,如果暴力在一種情況下是由國家決定的“正義”,那麼為什麼它在另一種情況下就不能是由個人決定的“正義”呢? 一個為死刑和戰爭辯護的社會如何才能防止其辯護延伸到暗殺和恐怖主義? 如果政府認為某些原因如此重要,足以證明殺害兒童是正當的,那麼它怎麼能希望阻止其邏輯蔓延到其公民或其公民的孩子身上呢?
如果我們賦予這些小荒謬以國際關係的重要性,那麼毫不奇怪,我們會產生一些更大的荒謬。 首先,還有什麼比我們對其他國家製造與我們製造的相同武器表示高度道德憤怒的態度更荒謬的呢? 正如我們的領導人所說,區別在於我們會善意地使用這些武器,而我們的敵人會惡意地使用它們——這一主張太容易符合一個不那麼尊嚴的主張:我們會為了我們的利益而使用它們,而我們的敵人會為了我們的利益而使用它們。會在他們的中使用它們。
或者我們至少必須說,戰爭中的美德問題就像亞伯拉罕·林肯發現戰爭中的祈禱問題一樣晦澀、模棱兩可和令人不安:“[北方和南方]都讀同一本聖經,向同一個上帝祈禱,每個人都向對方求助……雙方的祈禱都無法得到回應——任何一方的祈禱都無法得到完全回應。”
最近的美國戰爭既是“外國的”又是“有限的”,都是在幾乎不需要或不需要個人犧牲的假設下進行的。 在“外國”戰爭中,我們不會直接感受到我們對敵人造成的傷害。 我們在新聞中聽到並看到了這種損害的報導,但我們沒有受到影響。 這些有限的“外國”戰爭需要我們的一些年輕人被殺或殘廢,一些家庭應該悲傷,但這些“傷亡”在我們的人口中分佈如此廣泛,以至於很難被注意到。
否則,我們不會覺得自己參與其中。 我們納稅是為了支持戰爭,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我們在“和平”時期也繳納戰爭稅。 我們沒有經歷過短缺,我們沒有配給,我們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我們在戰時掙錢、借錢、花錢和消費,就像在和平時期一樣。
當然,我們不需要犧牲現在主要構成我們經濟的那些巨大的經濟利益。 任何公司都不需要遵守任何限製或犧牲一美元。 相反,戰爭是我們企業經濟的良藥和機遇,企業經濟靠戰爭生存和繁榮。 戰爭結束了1930 年代的大蕭條,從那時起,我們就一直維持著戰爭經濟——人們可以公正地說,這是一種普遍暴力的經濟——為此犧牲了巨大的經濟和生態財富,其中包括作為指定受害者的農民和產業工人階級。
我們對戰爭的執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這些代價被“外化”為“可接受的損失”。 在這裡,我們看到戰爭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和工業經濟的進步是如何相互平行的——或者,很多時候,僅僅是相同的。
浪漫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說大多數戰爭的辯護者,總是在他們的公開演講中暗示對戰爭的數學或解釋。 因此,據說北方因在內戰中遭受的苦難而為解放奴隸和維護聯邦“付出了代價”。 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自由是由愛國者的流血“買來”的。 我完全了解這些陳述的真實性。 我知道我是許多從其他人做出的痛苦犧牲中受益的人之一,我不想忘恩負義。 此外,我自己也是一名愛國者,我知道我們任何人都可能必須為了自由而做出極端犧牲的時刻到來——甘地和金的命運證實了這一事實。
但我仍然對這種會計方式持懷疑態度。 原因之一是,這必然是由生者代表死者完成的。 我認為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太容易接受或太容易感激他人做出的犧牲,尤其是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做出任何犧牲的話。 還有一個原因,儘管我們的戰爭領導人總是認為有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但從來沒有預先規定過可接受的水平。 最後,可接受的價格是支付的價格。
很容易看出這種對戰爭代價的計算與我們通常對“進步的代價”的計算之間的相似之處。 我們似乎已經同意,為所謂的進步已經(或將要)付出的任何代價都是可以接受的價格。 如果這個代價包括隱私的減少和政府保密的增加,那就這樣吧。 如果這意味著小企業數量的大幅減少和農場人口的實際毀滅,那就這樣吧。 如果這意味著採掘業對整個地區造成破壞,那就這樣吧。 如果這意味著一小部分人擁有的財富應該比世界上所有窮人擁有的財富還要多,那就這樣吧。
但讓我們坦誠地承認,我們所說的“經濟”或“自由市場”與戰爭越來越難以區分。 在上個世紀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擔心國際共產主義征服世界。 現在(到目前為止)我們不再那麼擔心了,我們正在見證國際資本主義對世界的征服。
儘管其政治手段(到目前為止)比共產主義溫和,但這種新國際化的資本主義可能對人類文化和社區、自由和自然具有更大的破壞性。 它的傾向同樣是完全的統治和控制。 面對新的國際貿易協定所批准和許可的征服,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和社區可以認為自己免受某種形式的掠奪。 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說任何形式的世界征服都是錯誤的。
他們所做的遠不止這些。 他們說,地方征服也是錯誤的,無論在哪裡,當地人都聯合起來反對。 在我所在的肯塔基州,這種反對派正在不斷增長——從西部,湖間之地的流亡人民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家園免遭官僚掠奪,到東部,山區的土著人民仍在掙扎。保護他們的土地免遭缺席公司的破壞。
擁有一個好戰的經濟,其目的是征服,幾乎摧毀它所依賴的一切,不重視自然或人類社區的健康,這是足夠荒謬的。 更荒謬的是,這種經濟在某些方面與我們的軍事工業和計劃如此契合,但在其他方面卻與我們聲稱的國防目標直接相衝突。
認為龐大的國防準備計劃應該首先建立在國家乃至地區經濟獨立的原則之上,這似乎是合理的、理智的。 一個決心保衛自己和自由的國家應該做好準備,並且始終做好準備,依靠自己的資源以及本國人民的工作和技能來生活。 但這不是我們今天在美國所做的事情。 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在以最揮霍的方式浪費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
目前,面對有限的化石燃料能源不斷減少,我們實際上沒有任何能源政策,無論是為了保護能源還是為了開發安全和清潔的替代能源。 目前,我們的能源政策就是充分利用我們擁有的一切。 此外,面對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我們幾乎沒有土地保護政策,也沒有對糧食初級生產者進行公正補償的政策。 我們的農業政策是用盡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同時越來越依賴進口食品、能源、技術和勞動力。
這些只是我們普遍對自己的需求漠不關心的兩個例子。 因此,我們正在闡述我們激進的民族主義和我們對國際“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擁護之間的必然危險的矛盾。 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荒謬呢?
我認為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顯然,如果我們能更好地照顧事情,我們就不會那麼荒謬了。 如果我們將公共政策建立在對我們的需求和困境的誠實描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對我們的願望的幻想描述之上,那麼我們就不會那麼荒謬了。 如果我們的領導人能夠真誠地考慮經過驗證的暴力替代方案,我們就不會那麼荒謬了。
這些話說起來很容易,但我們傾向於通過暴力來解決我們的問題,甚至享受這樣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原因,也是天性的原因。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有人至少必須懷疑,我們的生存權、自由權和和平權並不能得到任何暴力行為的保障。 只有我們願意讓所有其他人都生活、自由、和平,並且我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來實現這一點,才能保證這一點。 如果不能有這樣的意願,就只能屈服於我們所處的荒謬之中。 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樣,你不確定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
這是我一直在探討的另一個問題,一個現代戰爭的困境迫使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們願意接受多少其他國家的孩子因轟炸或飢餓而死亡,以便我們能夠獲得自由、富裕和幸福。 (據說)平安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沒有。 拜託,不要帶孩子。 不要為了我的利益而殺害任何孩子。
如果這也是你的答案,那麼你一定知道我們還沒有安息,遠未安息。 因為我們肯定會感到自己被更多緊迫的、個人的、令人生畏的問題包圍。 但也許我們也感到自己開始自由,最終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人類進步的最全面的願景,最好的建議,以及最少的服從:
“愛你的敵人,祝福那些咒罵你的人,善待那些恨你的人,為那些惡意利用你、迫害你的人祈禱; 使你們成為天父的兒女,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溫德爾·貝里 (Wendell Berry),詩人、哲學家和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在肯塔基州經營農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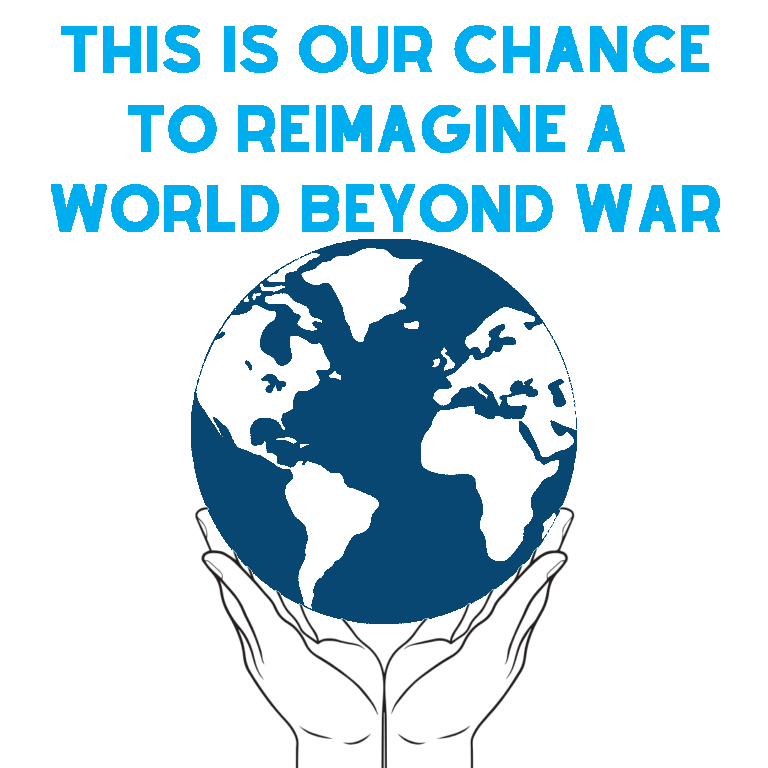







2回應
貝里對這種“生者代表死者”的會計方式的懷疑是絕對關鍵的事情。 愛國者和戰爭販子盲目地假設,認為所有在戰爭中陣亡的人和為戰爭“勝利”一方犧牲的人都是英雄,他們是正義和自願的,他們會再做一次,並且應該激勵每一代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是虛假和墮落的。 讓我們審問那些死者,如果我們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無法讓他們從死者中說話,那麼讓我們至少有禮貌地對他們的想法保持沉默,不要將我們的壞想法放入他們過早去世的思想和心靈中。 如果他們能說話,他們可能只是建議我們做出一些犧牲,以不同的方式解決我們的問題。
很棒的文章。 不幸的是,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關於戰爭如何摧毀戰爭製造者(我們)的所有觀點。 我們是一個充滿暴力的社會,因戰爭資源而陷入貧困,公民如此厭倦,我們的未來只能是自我毀滅。
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論後果如何都提倡增長和更多增長的體系。 好吧,這個系統只會導致一個臃腫的斑點,最終因其自身的過度行為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