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Hippolyte Eric Djounguep,24 年 2020 月 XNUMX 日
自2016年1922月以來,喀麥隆當局與兩個英語地區分裂分子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惡化。 這些地區自 1945 年(《凡爾賽條約》簽署之日)起受國際聯盟 (SDN) 管轄,自 1961 年起受聯合國管轄,並由英國管理直至 4,000 年。這場衝突被稱為“英語國家危機”,造成了嚴重傷亡:近 792,831 人死亡,37,500 人在國內流離失所,超過 35,000 名難民,其中 18,665 人流離失所。尼日利亞有 XNUMX 名尋求庇護者。
聯合國安理會於13年2019月19日首次就喀麥隆人道主義局勢舉行會議。儘管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立即停火以全面應對Covid-1960,但戰鬥仍在繼續惡化喀麥隆這些地區的社會結構。 這場危機是自 XNUMX 年以來喀麥隆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的一部分。這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無論從涉及的參與者數量、多樣性還是從其利害關係來衡量。 從某個角度感知的利害關係仍然反映了並不總是斷裂的聯繫,其中充滿了殖民歷史的圖像和不合時宜的表現,以及多年來尚未完全發展的視角。
一場與現實交錯的先驗衝突
對非洲衝突的看法是通過多種機制建立的,其中一些機制經常得到媒體和其他知識轉讓渠道的響應。 國際甚至國家媒體的邊緣媒體描述喀麥隆英語危機的方式仍然揭示了一種正在努力擺脫據稱受到監督的願景的話語。 有時充滿陳述、陳詞濫調和獨立前偏見的言論至今仍在繼續。 世界上甚至非洲的一些媒體和其他知識傳播渠道維持著棱鏡和範式,使非洲的殖民和後殖民形象得以蓬勃發展。 然而,這些對非洲大陸的刻板印象掩蓋或破壞了另一種媒體類別的劃分努力:知識分子和學者不會被這種後殖民願景所迷惑,他們選擇了經過驗證的信息和問題,使非洲這個由54個國家組成的大陸與世界上其他大陸一樣複雜。
喀麥隆的英語危機:如何界定它?
一些國際媒體小報和其他廣播渠道將英語危機描述為屬於被標記為“自然災害”的事件組——這是對媒體所知的非洲經常發生的社會事件的簡單限定和歸化。 由於認識不足,他們“歸咎於”喀麥隆首都雅溫得政權的“長期執政和消極治理導致了戰爭”。 喀麥隆共和國國家元首保羅·比亞在所有負面行為中都被提及:“缺乏政治道德”、“治理不善”、“總統沉默”等等。值得關注的不是報導事實的真實性和嚴重性,而是某些言論缺乏替代解釋。
民族問題?
這場非洲大陸戰爭的自然化是通過種族因素的喚起而展開的,這是今天仍在繼續的關於非洲的殖民話語的一個基本方面。 這種衝突最終被認為只是一種自然現象的原因,更廣泛地位於一個反對自然和文化的軸心上,我們在某些文獻中找到了各種不同的喚起。 “英語國家危機”通常被描述為一種無法理性或幾乎無法解釋的現象。 在解釋戰爭時傾向於自然原因的觀點常常發展出本質主義的論述。 這通過與演講混合而強化了世界末日的形象,其中我們特別發現了“地獄”、“詛咒”和“黑暗”等主題。
應該如何評價呢?
這種評估更加定期,有時在某些媒體和知識傳播渠道的重要部分中決定。 從1年2017月XNUMX日英語危機的僵局開始,人們就理解“這可能會導致喀麥隆政治新的分裂,以及植根於部落忠誠或部落之間地獄戰爭的當地民兵的蔓延”。 非洲現在正在註視著喀麥隆。 但要注意:“部落”和“族裔群體”等術語充滿了刻板印象和既定觀念,並且使事物現實的實質脫鈣。 這些話,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已經接近於野蠻、野蠻、原始。 應該指出的是,在一種描述中,戰鬥並不反對派系選擇戰爭選項來損害另一派系,但它們似乎強加於他們,因為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訓練有素”。
一連串負面詞語
“英語危機”通常會出現混亂、混亂、搶劫、喊叫、哭泣、流血、死亡的場景。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武裝團體之間發生戰鬥、軍官進行行動、交戰各方發起對話的嘗試等等。其優點的問題最終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個“地獄”沒有任何基礎。 人們可以理解,“喀麥隆是國際組織幫助非洲解決戰爭的努力的嚴重挫折”。 特別是“根據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喀麥隆的英語危機是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影響了約 2 萬人”。
也有創傷圖像
誠然,有一類媒體聲稱“喀麥隆的衝突是可怕而復雜的”。 這些痛苦是真實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難以言表的。 此外,面對非洲特有的、沒有人真正負責的致命事件,對這些苦難的常規描述(我們沒有解釋其原因)尤其富有同情心。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談到世界各地的電視新聞圖像時分析道,這樣的敘述最終構成了“一系列看似荒謬的故事,最終都以相同的方式結束(……)‘事件的出現無需解釋,將消失無解’。” 對“地獄”、“黑暗”、“爆炸”、“噴發”的提及有助於將這場戰爭歸入一個單獨的類別。 無法解釋的危機,理性上無法理解的危機。
圖片、分析和評論暗示著痛苦和痛苦。 在雅溫得政權中,缺乏民主價值觀、對話、政治意識等。他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他所描繪的形象的一部分。 也可以把他形容為“才華橫溢的策劃者”、“有能力的組織者”、有一定技能的管理者。 人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儘管經歷了許多曲折,但仍能維持一個政權超過35年,這一事實足以為他贏得這些資格。
新基地合作
喀麥隆英語危機的歸化、國際干預的解決方案以及某些媒體講話中衝突各方的聲音和不和諧聲音的消失,都揭示了兩國關係和獨立後權力的持久存在。 但挑戰在於發展新的合作。 誰說新合作說明非洲新願景。 因此,有必要將非洲的目光政治化,抓住重點,引導一場沒有種族偏見、陳詞濫調、成見的反思,最重要的是超越“情感是黑人,理性是希臘人”的桑戈爾式思想。
一句話多不幸又不無分身。 桑戈爾的著作不應該被簡化為這種斷章取義的說法。 不幸的是,許多專制和極權主義非洲國家幾十年來一直接受席捲整個非洲(從北非到南非)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思想和偏見。 其他領域也未能倖免,也未能逃脫大量先驗和表徵:經濟、人道主義、文化、體育甚至地緣政治。
在當代非洲社會,人們對看到的東西比聽到的東西更敏感,闡釋的“手勢語言”是分享令人興奮的、創新的和高質量的東西的一種非常寶貴的方式。 存在的根源在於世界正在發生的挑戰、演變和轉變所帶來的第一個“是”。 這些是支撐期望的要求。 作為不受控制的權力的標誌,媒體的言論希望突出新聞的所有組成部分,以實現體面和協調的發展。
國際媒體上發展起來的信息流,以及由於分析的深度而質量可見的研究,這些都讓我們遠離自我,讓我們不再擔心自我辯護。 他們呼籲讓信息改變國家,對習慣進行“心理分析”,使之與全球化接軌。 因此,按照媒體言論的解釋,“分析同時是接收、承諾和發送”; 僅保留三個極點之一併不能解釋分析的運動本身。
然而,所有的功勞都歸功於國際媒體、學術界和科學界的某些人士,他們有責任提供一個標誌和一個詞,表明非洲的利害關係和雄心壯誌已經擺脫了陳舊的範式。 後者不應該做出一種神奇的舉動來迫使環境有利於非洲; 這也不意味著非洲大陸的所有項目都獲得批准。 因為它指的是使一切煥然一新的戰略信息,因為它創造了對未來的信心,所以它們是和平與希望的真正源泉; 他們開啟未來,引導新的生活動力。 它們還證明了失敗和成功中都存在幸福。 在有把握的行軍和流浪中。 它們既不提供人類生活的不確定性,也不提供項目或責任的風險,而是支持對更美好未來的信心。 然而,這不是一個將合法的多樣性與信念和個人實踐的並置(簡單多元化)相混淆的問題,也不是通過將一種信念和獨特的實踐強加於所有人(統一性)來同化感官的統一性的問題。
這種非洲形像不僅是外生的,而且只能經歷過; 它也是聯合製作的,有時是在非洲大陸內部上演的。 這不是陷入“地獄,是別人”的陷阱的問題。 每個人都面臨著自己的責任。
Hippolyte Eric Djounguep 是法國雜誌 Le Point 的記者和地緣政治分析師,也是 BBC 和赫芬頓郵報的撰稿人。 他是多本書的作者,包括《喀麥隆——英語國家危機:殖民後分析論文》(2019 年)、《非洲經濟地理》(2016 年)、《衝突視角》(2014 年)和《媒體與衝突》(2012 年)等。 自2012年以來,他對非洲大湖地區、非洲之角、乍得湖地區和科特迪瓦的衝突動態進行了多次科學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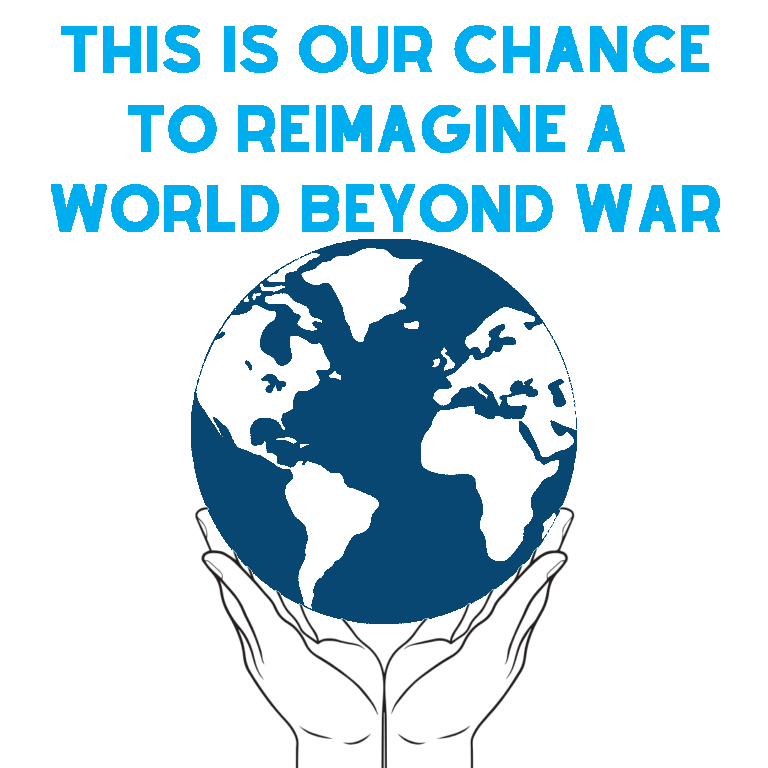







一個響應
得知法屬喀麥隆軍隊繼續殺害、搶劫、強姦等無辜的安巴佐尼亞英語人民,他們正在尋求恢復合法獨立,這真是令人悲傷。 由于冠狀病毒襲擊世界,聯合國秘書長宣布停火,但法屬喀麥隆政府繼續襲擊、殺害、摧毀安巴佐尼亞人。
最可恥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對公然的不公正行為視而不見。
安巴佐尼亞決心與新殖民主義作鬥爭並使其擺脫新殖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