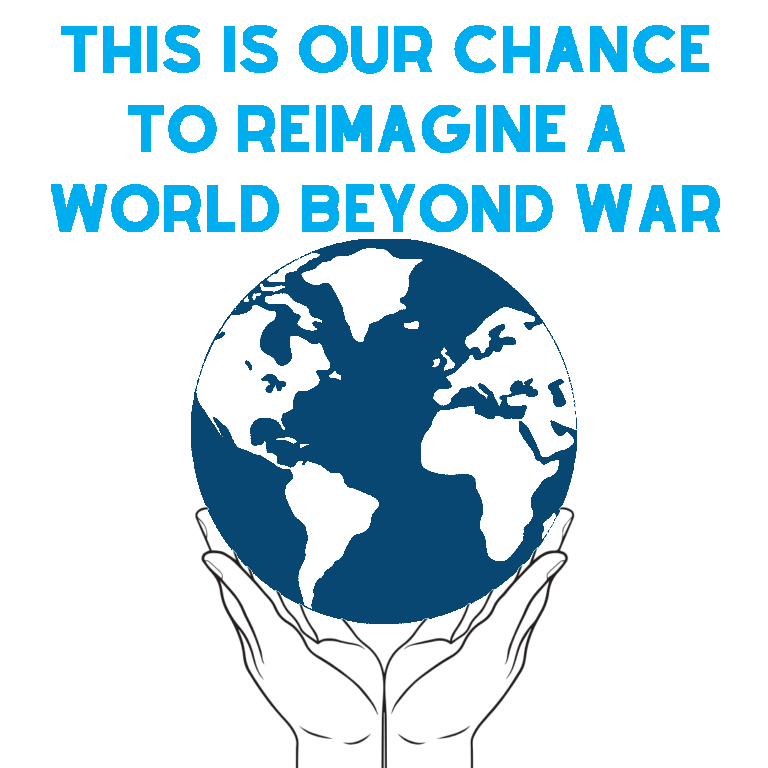安德魯·莫斯
1946 年,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在他的經典文章《政治與英語》中譴責了對語言的濫用,他著名地宣稱“它[語言]變得醜陋且不准確,因為我們的思想是愚蠢的,但我們語言的不嚴謹使得它變得更容易”讓我們有愚蠢的想法。” 奧威爾將最尖銳的批評保留在腐敗的政治語言上,他稱之為“為站不住腳的人辯護”,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其他作家也對政治話語進行了類似的批評,並根據當時的情況調整了焦點。
一項特別的批評集中在核武器的語言上,我認為這種語言應該引起我們今天的特別關注。 它被批評者稱為“核武器言論”,是一種高度軍事化的言論,掩蓋了我們政策和行動的道德後果。 它是軍事官員、政治領導人和政策專家以及記者和公民使用的語言。 這種語言像入侵物種一樣滲透到我們的公共討論中,給我們思考集體現在和未來的方式投下陰影。
例如,在《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較小的炸彈加劇了核恐懼兩位《紐約時報》記者威廉·J·布羅德(William J. Broad) 和戴維·E·桑格(David E. Sanger) 描述了奧巴馬政府內部正在進行的有關所謂核武庫現代化的爭論,這種轉變將導致原子彈具有更高的精度和能力。操作員可以增加或減少任何單個炸彈的爆炸能力。 支持者認為,武器現代化將增強對潛在侵略者的威懾力,從而降低使用它們的可能性,而批評者則聲稱,升級炸彈將使它們的使用對軍事指揮官更具吸引力。 批評者還提到了現代化計劃的成本——如果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成本高達 1 萬億美元。
在整篇文章中,布羅德和桑格用 Nukespeak 的語言闡述了這些問題。 例如,在下面的句子中,它們包括兩個委婉說法:“其產量,即炸彈的爆炸力,可以根據目標調高或調低,以盡量減少附帶損害。” “屈服”和“附帶損害”等委婉說法將人類的存在——聲音、面孔——從死亡的等式中抹去了。 儘管作者確實將“產量”一詞定義為“爆炸力”,但該詞在文本中的出現仍然令人不安,因為它的良性含義(即收穫或金錢利潤)與致命收割的惡魔意義之間的對比。 “附帶損害”這個詞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純粹的謊言,它忽略了任何考慮中難以言喻的事情。
這句話還包含了核武器語言的另一個特徵:對致命小玩意的非道德迷戀。 一個人調低家裡的恆溫器是一回事;調低家裡的恆溫器是一回事;調低家裡的恆溫器是一回事。 “減少”死亡的有效載荷是另一回事。 當我教授關於戰爭與和平文學的本科課程時,我和我的學生在我們的一個單位學習廣島和長崎的文學。 我們閱讀了杜魯門總統關於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聲明,探討了杜魯門如何討論這種新武器的起源以及使其成為“歷史上有組織的科學的最偉大成就”的科學合作。 與此同時,我們閱讀了日本作家的故事,他們在地獄中倖存下來並仍在繼續寫作。 一位這樣的作家太田洋子(Yoko Ota)讓她的短篇小說《螢火蟲》的敘述者在原子彈爆炸七年後回到廣島,遇到了許多倖存者,其中包括被原子彈嚴重毀容的年輕女孩光子(Mitsuko )。爆炸。 儘管毀容讓她在公眾面前感到痛苦,但美津子表現出了非凡的韌性和“渴望更快成長並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的願望”。
精神病學家兼作家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寫道,即使在核陰影下,我們也可以在傳統的“預言家的智慧中找到救贖的可能性:詩人、畫家或農民革命者,噹噹前的世界觀失敗時,他們扭轉了世界觀。”他或她的想像力像萬花筒一樣,直到熟悉的事物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模式。” 利夫頓於 1984 年寫下了這些話,從那時起,全球範圍內的合作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 今天,和以前一樣,藝術家和預言家能夠認出隱藏在核話謊言背後的人類存在。 藝術家和預言家能夠找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這種所謂的理性中存在著瘋狂——而事實上,我們有能力找到另一種方式。
安德魯·莫斯 (Andrew Moss),聯合組織 PeaceVoice, 是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的名譽教授,他在那裡教授“文學中的戰爭與和平”課程長達 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