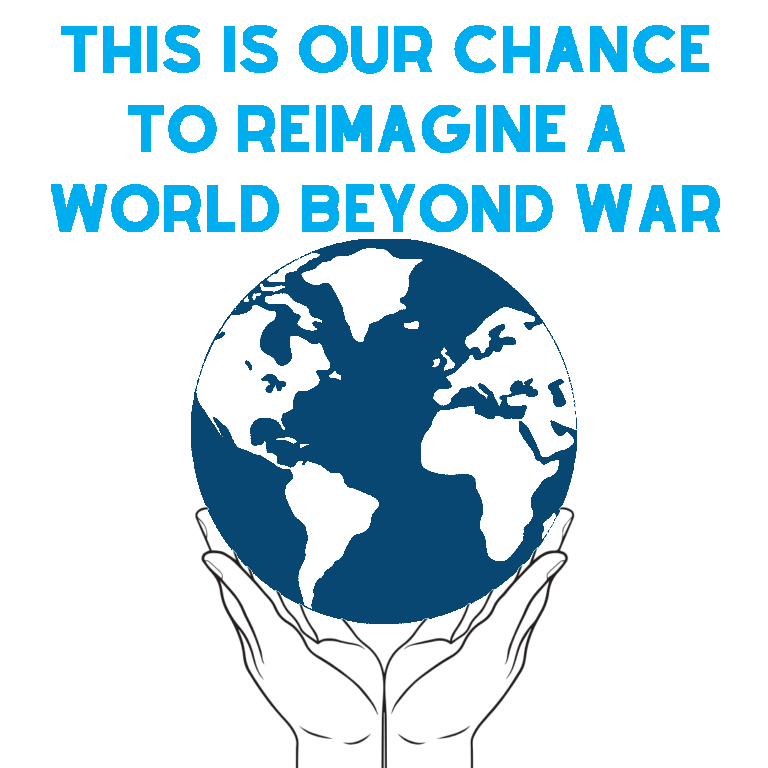安迪·潘恩,August 23,2017。
16 年 2016 月 XNUMX 日星期五對我來說是忙碌的一天。 我開始準備一個關於 Pine Gap 的廣播節目,Pine Gap 是澳大利亞中部愛麗斯泉附近的一個秘密美國軍事基地。 我採訪過一位研究 Pine Gap 及其用途的學者。 反對它的積極分子; 阿倫特 (Arrernte) 的一位傳統業主表示,該公司無權在那裡。 然後我趕往格里菲斯大學,在那裡我在道德課上做客座演講,主題是公民不服從——故意和公開違反不公正法律的行為。
但我並不是純粹報導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記者,也不是純粹解釋理論的學者。 因此,在完成這兩項任務後,我坐上汽車前往愛麗絲泉,試圖抵抗松峽及其引發的美國戰爭。
所以我想在我們繼續之前,先快速了解一下 Pine Gap 及其用途。 如果您感興趣的話,還有更多信息,但基本上,松峽是美國在全球戰略性部署的三個衛星通信基地之一,以便能夠監視全世界。 它的租約於 1966 年簽署,基地於 1970 年建成。起初,它從未公開承認它是一個軍事設施——它被描述為一個“太空研究站”,直到學者德斯·鮑爾發現了它的實際用途。 有傳言稱,總理高夫·惠特拉姆被解僱與他希望獲得對基地的更多控制權並與中央情報局站在一起。
在其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儘管 Pine Gap 一直吸引著反戰活動人士的關注,但其目的只是基本的監視。 但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目的發生了變化。 如今,松峽通過衛星接收到的手機和無線電信號被用於無人機襲擊或其他有針對性的爆炸——使美國能夠在中東殺人,而無需擔心士兵被殺——或者避免同情心的風險。來自與真實的人的互動。
正如我所說,松峽多年來一直是無數抗議活動的主題。 這次活動是為了紀念租約簽署 50 週年——儘管大家前往沙漠的具體目的尚不清楚。 稍後會詳細介紹。
去愛麗絲的旅程是乘坐我朋友吉姆的貨車。 吉姆 (Jim) 是愛麗絲 (Alice) 眾多訴訟和法庭案件的資深人士 - 他非常熟悉這條路線。 吉姆用用過的魚薯條油製成的生物柴油被運往貨車。 因此,所有可用的汽車空間都被裝滿燃料的桶佔據了。 其他旅伴是我的室友弗朗茲和蒂姆。 弗蘭茨是吉姆的兒子,所以儘管他還是個青少年,但他從小就參加抗議活動。 蒂姆來自新西蘭; 他之前在澳大利亞的反戰公民抗命行為導致他在維多利亞州天鵝島遭到英國特種空勤團 (SAS) 士兵的襲擊、脫光衣服和威脅。 他沒有被嚇倒,而是回來尋求更多。
對於我們這些室友(事實上吉姆也是如此,他幾十年來一直住在類似的天主教工人房屋中),長途跋涉 3000 公里去抗議只是我們努力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和和平的世界的一部分。 住在一起; 我們努力以社區和可持續的方式生活,向需要訪問或住宿的朋友和陌生人敞開大門,並公開為我們所信仰的世界鼓動。
另一位旅伴是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人,但他聯繫我們尋找搭便車的機會。 他是一個健談的人,不一定與我們其他人有相同的談話品味或相同的價值觀。 這很好,但只是在四天的旅行中進行了一些測試。
我們開了四天車。 對於沙漠來說,雨確實很大。 在伊薩山,我們睡在教堂後陽台的遮蓋下,在溢出的排水管下淋浴。 在那裡,我們還短暫會見了來自凱恩斯的車隊,他們也正前往愛麗絲。 他們度過了一段炎熱的天氣,正在自助洗衣店烘乾他們的東西。 我們的朋友瑪格麗特也在其中。 另一位長期的和平活動家,長期以來一直試圖組織一場行動。 我們討論了一會兒策略然後又上路了。
即使在雨天,沙漠駕駛當然也很壯觀。 開車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景色在變化——樹木越來越稀疏,牧場也從鬱鬱蔥蔥變為零星分佈,主色調從綠色變為紅色。 我們在魔鬼彈珠處停下來,攀爬那些非凡的反重力岩石。 我們凝視窗外,欣賞澳大利亞中部美麗的色彩和廣闊的地平線。 即使在我們狹窄的車裡,我們也感覺像是從城市的幽閉恐懼症和壓力中解脫出來。
週一下午我們進入了愛麗絲。 我們驅車穿過城鎮到達南側的克萊潘斯(Claypans),那裡是治療營的所在地。 設立了一個大概有40-50人的營地; 其中包括另一位老和平活動家格雷姆,他打開水壺,用茶歡迎我們大家。
在這一點上,我可能應該離開敘述來解釋松樹峽的這種融合是如何組成的。 正如和平運動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它並不完全和平。 幾年前,在年度獨立與和平澳大利亞網絡聚會上,我第一次聽到了討論融合的想法。 IPAN 是一個和平團體聯盟,每年組織一次會議,主要由學者和活動家就有關戰爭和軍國主義的各種主題進行演講。 它相當不錯,但不涉及太多破壞性的麻煩,這更有趣,也更吸引媒體關注。 為此,成立了一個名為“Disarm”的組織,其想法是建立一個露營地和一個空間,供人們進行可能破壞 Pine Gap 平穩運行的行動。
除了這兩個標註之外,阿倫特人克里斯·湯姆林斯認為他的傳統土地上已經發生了足夠的殺戮。 不過,他希望的回應與其說是抗議,不如說是一個“治療營”——他的願景似乎是一個無限期的有意社區,其中包括從傳統原住民文化到永續農業和冥想的一切。 他走遍全國分享這個想法——主要是在 Confest 和 Nimbin's Mardi Grass 等嬉皮士活動中。
首先開始的是治愈營。 設立這個營地的目的是吸引那些相信精神治療並特別重視傳統原住民儀式理念的人們。 但有趣的是,那些對土著文化的內部政治抱有很大興趣的人卻因為阿倫特內部似乎存在一場爭論而感到厭煩,爭論的焦點是克里斯·湯姆林斯是否有權代表他們說話或使用克萊潘斯的土地。 有點亂的生意。
來到營地後,很快就發現這裡住滿了生活在新南威爾士州北部(我認為大多數人實際上來自那裡)或彩虹聚會的人 - 熱衷於替代醫學、閱讀能源和生活與自然和諧相處。 不幸的是,他們也是那種容易大量使用毒品、尷尬的文化挪用以及缺乏對自己特權的認識的人,這些特權使他們相信和平與繁榮可以來自於靜坐冥想。 這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這種文化,並且認為這對於嘗試創造社會變革甚至豐富社會互動沒有多大幫助。 我很快推測這就是我們這裡面臨的情況。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營地閒逛了幾天,並試圖做出貢獻。 這是一個奇怪的群體,但那裡有一些好人。 隨著其他人也開始加入,我們開始討論行動和媒體的策略。
 瑪格麗特提議的行動是在松峽現場“哀悼”,以哀悼所有在此地造成的死難者。 她提出了創造性的詮釋——音樂、舞蹈、藝術。 我個人覺得我想要一張與停止 Pine Gap 的運營更直接相關的圖像。 我聽說鎮上有一個車站,巴士從那裡出發,將所有工人送往基地。 我設想將其鎖定並位於市中心,靠近媒體和路人。
瑪格麗特提議的行動是在松峽現場“哀悼”,以哀悼所有在此地造成的死難者。 她提出了創造性的詮釋——音樂、舞蹈、藝術。 我個人覺得我想要一張與停止 Pine Gap 的運營更直接相關的圖像。 我聽說鎮上有一個車站,巴士從那裡出發,將所有工人送往基地。 我設想將其鎖定並位於市中心,靠近媒體和路人。
因此,當其他人尋找在基地行走的潛在路線時,我進城去尋找倉庫。 原來它有四個門——對於一個人和他的鎖定裝置來說關閉有點多。 我需要一個B計劃。
儘管如此,進城偵察還是有它的好處的——它讓我脫離了越來越沒有吸引力的治療營。 來到愛麗絲我就知道那裡有幾個老朋友,很高興見到他們。 但進城後的一個驚喜是,我發現實際上有一大堆來自全國各地的熟悉面孔——其中一些人我已經好幾年沒見過了(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在沙漠中間——我有上次來愛麗絲是五年前)。
其中一些人只不過是熟人,但通過與人們進行政治活動,你會獲得一種特殊的聯繫。 其一,與人一起從事一個項目或行動,即使是短暫的,也與幾次遇到某人有很大不同。 其次,有時這些情況可能會有點緊張或走向情緒的極端。 這可以起到快速建立牢固聯繫的作用。 第三,知道你們有相同的價值觀,並且對方可能一直在做你支持的事情,這意味著存在一種本能的信任和團結。
也許正是這些原因,或者也許無論如何它們都是如此; 但當我問我是否可以在計劃行動時去那裡時,有一個家庭非常熱情。 事實上,這個問題得到了強調,暗示著對我不受歡迎的想法感到震驚。 我試圖向他人提供這種全面的款待,而且也經常受到這種款待。 每一次都一樣值得讚賞。
所以我呆了幾天,在後院露營,並在城裡找事情可做,因為我不太想回到營地。 我出去閒逛,在房子周圍幫忙,在一個為當地孩子提供的臨時服務中心工作了一天,粉刷牆壁和建造籃球筐,一些朋友為“食物不是炸彈”(Food Not Bombs)(免費的街頭餐,是我的生活之一)負責運營、做飯和打掃衛生。最喜歡的東西,並且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約六年了)。
熱情好客的人和我可以貢獻的東西讓我很容易在愛麗絲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真的很享受在那裡的時光。 那裡有一種有趣的對比——這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小鎮,對於那些聲稱想要幫助原住民、只是為了待上幾年、賺了很多錢然後返回的人,理所當然地有很多憤世嫉俗的態度。海岸。 有一次,我和兩個剛認識的人坐下來喝茶。 我們談論了我們四處走動的傾向,我們都將這種特徵視為一種弱點。 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些人一生都在一個地方度過,但卻從未真正對周圍的人做出承諾。 成為一名漂泊者,並做好漂泊者,並不是永遠不在家,而是永遠在家。
當我在城裡時,我的同伴(以及忍受治療營的人)一直在準備哀悼。 週日晚上他們出發了。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群體——六個人,每個人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七十多歲。 他們半夜在灌木叢中走了幾個小時,打算在黎明時分走到松峽領地並進行哀歌。 他們到達了外門(基地本身安全良好,燈火通明,但松樹峽的實際財產非常大,大部分由空灌木叢組成),當時天還黑,他們休息了一會兒,等到黎明。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被警察的車頭燈吵醒了——不知怎麼的,他們被發現了,現在被包圍了。 他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無論如何,警方也不太熱衷於進行太多逮捕和免費宣傳。 於是他們全都被送上了警車,開回了營地。
 第二天早上,三位貴格會老奶奶舉辦茶會,暫時封鎖了松峽的正門。 這是他們一年前在淺水灣美澳聯合軍事演習期間採取的行動的一次重複。 友善的老婦人喝茶、擋路的場景總是引起一些關注。 他們已經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但警察似乎又不想這麼做——他們周圍的交通被改道,最終他們拿起茶壺回家了。 但這是融合的第一次公開行動。
第二天早上,三位貴格會老奶奶舉辦茶會,暫時封鎖了松峽的正門。 這是他們一年前在淺水灣美澳聯合軍事演習期間採取的行動的一次重複。 友善的老婦人喝茶、擋路的場景總是引起一些關注。 他們已經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但警察似乎又不想這麼做——他們周圍的交通被改道,最終他們拿起茶壺回家了。 但這是融合的第一次公開行動。
我們重新聚在一起討論後備計劃。 哀嘆者渴望在某個時候再次嘗試。 我分享了我的計劃——我想把自己鎖在松峽前門一輛載著工人的公共汽車的底盤上(同樣,前門距離基地很遠,並不是真正的步行距離)。 我們把日期定在周三早上。
回到布里斯班,為旅行做準備,我給自己買了一輛 D-Lock 自行車。 65 美元,這是一把便宜的鎖,但仍然是我五年多來買過的最貴的單件物品(這不是我編造的)。 它是一個一次性物品——我的計劃是用它把自己鎖在某個東西上,直到一名警察被迫用角磨機測試它的強度。 週二晚上,在微調我的媒體發布後,我花了至少一個小時練習將自己鎖定在不同車輛的車軸上。
當我們談論這一行動時,有幾個人對我在公共汽車下滑行的安全表示擔憂。 我並不擔心這個,也不擔心被捕; 但我很擔心是否能及時鎖定自己。 我參與過的任何其他鎖定都是在充足的時間和空間內完成的——而不是在警察面前。 另外,因為這是我唯一帶的東西,所以我會在脖子上使用 D 型鎖,而不是更實用的雙臂肘鎖。 路上唯一的阻塞點(我希望能攔住整個車隊,而不僅僅是一輛公共汽車)就在前門,那里肯定有警察。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讓他們措手不及。
我因緊張而無法入睡。 我只是不停地想像可能會發生什麼。 終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兒後,我的鬧鐘響了,太陽仍在地平線以下,傾盆大雨敲打著帳篷。 是時候該走了。
警察已經在門口等候了。 前一天早上我們做了一次假跑,只是舉著標語,所以我的鎖藏在我的毛衣下面,我們假裝我們只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公共汽車到了。 就在這時,我的朋友們舉著橫幅走到前面。 公共汽車停在我面前。 警察就在大約20米遠的地方。 經過一番緊張之後,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我滑到公共汽車下面,仰面朝前軸蠕動。 我把鎖放在吧台上,把脖子伸進去,然後去把鎖關上。 然後有雙手抓住了我。 我拼命地抓住車軸,但沒有用。 三個警察把我的屍體拖了出去。 他們拿走了我的鎖,但又放了我,讓我渾身濕透地躺在路上,羞澀地看著公交車開進來。
警察們也有些尷尬。 當其餘的公共汽車通過時,他們現在排列在道路兩側。 其中一個站在我面前幾米遠的地方,竭盡全力地瞪著我,令人生畏。 最終,有人找到我,記錄了我的詳細信息,並告訴我,我可能會被罰款。
所有公共汽車都通過後,我們成群結隊地回到解除武裝營地,營地現在已經設立在距大門幾公里的地方。 我渾身濕透,有點失望,但腎上腺素仍然很高。 回到營地,我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些早餐,然後坐下來參加帳篷大會,會議計劃在當天下午大規模封鎖道路。
帳篷大會冗長而混亂——太多的人彼此不認識,並且在一個空間裡有不同的想法。 討論一直進行著。 最終達成了一些解決方案,但此時我感到很冷,早上失敗的失望開始襲來。我們回到治療營放鬆一下。
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真正去過營地了,在那段時間裡,這裡似乎變得更加陌生了。 毒品使用量很高——有很多雜草,但顯然也有蟾蜍的體液。 這些理論也遠遠超出了通常的嬉皮士光環和良好的氛圍。 令人費解的是,現在營地裡的大多數人似乎都相信有外星人計劃來到地球並迎來一個新社會,但他們必須等到世界足夠和平才能來到松樹峽並簽署星際條約。 抗議 Pine Gap 是一個壞主意(儘管我們來這裡就是為了這樣做),因為它會讓條約面臨風險。
我從來沒有完全掌握這個理論的所有細微差別,但我發誓這不是我編造的。 一個人走過來告訴我們,他向愛麗絲出櫃,相信人類應對戰爭負責,我們應該抗議松峽,但前一天晚上他是否相信了這一理論的錯誤。 對此你應該說什麼? 治療營裡有一些好人,但大多數都很糟糕。 我可以只寫一篇關於治愈營的報導,這會有點幽默,但這並不是重點,而且當時經歷它已經夠難的了,現在不復述它了。 每個激進的政治團體都有其古怪的想法,但這是另一個層面。 不管怎樣,此後我們在營地待的時間並不多,我不能說我錯過了它。
與此同時,除了第一次嘗試中失去的幾名成員外,哀悼者正計劃再次嘗試進入基地。 由於我的 A 計劃失敗了,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就是那天晚上加入他們。 這確實讓人鬆了一口氣。 與早上的緊張相比,半夜在灌木叢中漫步幾個小時會讓人放鬆。 另外我會和我的朋友們在一起!
不過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是下午的路障。 這是一個有趣的動作,展示了警察的策略——警察沒有逮捕任何人,甚至沒有讓我們繼續前進。 前往 Pine Gap 的交通從後門改道; 不僅抗議者被允許留在路上,警察還親自封鎖了路的盡頭,不讓我們出去。 這引發了一些關於警察加入我們封鎖的笑話,但這確實給我們這些需要出去計劃下一步行動的人帶來了一些問題。 最後我們三個人不得不步行到路的盡頭,帶著我們需要的任何東西,然後搭便車回城。
哀悼前的交匯點  心中的篝火是愛麗絲郊區的一處精神靜修所,他們每週都會在那裡聚餐和討論。 今晚的主題是“信仰與行動主義”。 周圍的人有著不同的觀點,但當然我們沒有提及的是我們即將進行的精神實踐——進入巴比倫眼中的朝聖,冒著入獄的風險公開聲明抵抗美國對世界的軍事統治。 耶穌說:“收起你的刀吧,因為靠刀劍活著的人,必死於刀劍之下。” 對我來說,信仰和政治行動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即將離開的朝聖之旅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活動。
心中的篝火是愛麗絲郊區的一處精神靜修所,他們每週都會在那裡聚餐和討論。 今晚的主題是“信仰與行動主義”。 周圍的人有著不同的觀點,但當然我們沒有提及的是我們即將進行的精神實踐——進入巴比倫眼中的朝聖,冒著入獄的風險公開聲明抵抗美國對世界的軍事統治。 耶穌說:“收起你的刀吧,因為靠刀劍活著的人,必死於刀劍之下。” 對我來說,信仰和政治行動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即將離開的朝聖之旅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活動。
於是我們開始準備。 我們有幾個朋友同意開車送我們到一個可以步行去松峽的地方。 不過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情要處理——這次不是媒體,而是交給了其他幾個朋友。
第一次入侵嘗試失敗後,人們就如何發現該組織展開了很多討論。 一個看似不太可能但仍然受到認真對待的建議是,松峽對全球熱傳感器衛星跟踪的訪問(用於探測導彈發射,顯然也是為了跟踪氣候變化)已經發現了一群正在等待的熱血人類在基地的外圍圍欄處。 緩解這種情況的建議是這次更加分散(這樣我們就可以成為袋鼠或其他什麼東西),並佩戴塑料緊急保暖毯來捕獲我們的身體熱量,而不是輻射它以供檢測。 我一直反對戴閃亮的塑料毯子,但當其他人都穿上一條時,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我拒絕並且我們再次被發現,那將是我的錯。 我害羞地把自己裹在一件看起來像鋁箔套裝的衣服裡,然後把夾克套在上面。 為了和平我們必須做出的犧牲。
我們在星光的照耀下出發,在寂靜中(除了沙沙作響的塑料聲)。 當我們走了不到 500 米時,第一個混亂的時刻到來了——我們靠近一棟房子,狗在吠叫。 有人說停車,但前面的人卻在超速前行。 我們分開了。 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開始。 我們等了一會兒,嘗試各種嘗試找到其他人,同時又不引起我們太多的注意。 最後我們繼續走,(最終正確地)其他人會在一個顯眼的地標處等我們。
這是一段很長的步行路程。 前一天晚上我幾乎沒睡,現在已經過了午夜了。 但我艱難地前行,雖然有點困,但仍有足夠的腎上腺素繼續前行。 有趣的是,腎上腺素並不是因為我們被捕後可能發生的事情而緊張,儘管我知道我們面臨著長期監禁的風險。 我幾乎沒有想到這一點。 更多的是與一群同志一起潛行沙漠執行和平使命的興奮。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各地的軍事基地都有“和平朝聖”的傳統,以見證和平——其中大多數是基督徒,他們將和平主義與公開反對軍國主義的神聖旅程的宗教傳統結合起來。 在松峽 (Pine Gap)、昆士蘭州淺水灣 (Shoalwater Bay),美國和澳大利亞軍隊在這裡進行聯合訓練演習;在天鵝島 (Swan Island),英國特種空勤團 (SAS) 計劃執行特殊任務。 我是朝聖想法的粉絲——我們公開破壞了戰爭準備工作,但漫長的旅程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反思在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的社會中為和平而生活意味著什麼。
另外,我還可以反思與我一起朝聖的人們。 我很自豪能和他們一起散步。 吉姆和瑪格麗特都是長期活動家——他們在我出生之前就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既是我的靈感,也是我的朋友——因為他們在失敗和幻滅中表現出了對這一事業的奉獻精神; 通過為人父母和時間的流逝。 我之前曾多次因同一原因與他們一起被捕。
然後是蒂姆和弗朗茲——我的室友。 我們不僅共享空間、食物和資源; 儘管我們確實分享它們。 我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夢想——我們選擇嘗試以一種不同於我們周圍文化的方式生活,作為我們周圍以自我為中心、以金錢為中心的世界的避難所; 作為可能的不同方式的見證人。 現在,作為該項目的延伸,我們一起走進世界軍事超級大國的關鍵基地之一,並一起行動。
儘管如此,步行有時還是很艱難。 我們走上山下。 腳下的岩石和三齒稃草是如此鋒利,就連吉姆這個從來不(我是說從來不)穿鞋的人,也穿著他在家裡找到的一雙慢跑鞋(它們可能屬於他的一個孩子)。 瑪格麗特一直在找一位私人教練,試圖讓她適應這次步行,但她也因試圖做到這一點的所有其他工作而精疲力盡——會議、計劃、媒體發布、協調。
對於她和其他人來說,這是四天內第二次進行這種特殊的深夜散步。 瑪格麗特感到疲倦並失去平衡。 當我們走下山時,她抓住我的手臂以穩定自己。
一路上我們停了幾站。 為了遵守熱傳感器的預防措施,我們會分散開來停下來。 我會躺下來仰望星空,就像我在出城的任何夜晚所做的那樣。 今晚雖然不像往常那麼令人滿意。 其一,松峽的巨大燈光造成了光污染,使得星星不像沙漠中通常那樣令人印象深刻。 然後是流星——通常這是一個令人愉悅的景象,但今晚我就像比利·布拉格一樣,認為它們可能是衛星。 松樹峽用來殺害世界另一端人民的衛星。
無論如何,我們繼續前行。 對我們所在位置的輕微誤判意味著我們不必要地登上一座非常大的山丘,然後又下山。 雖然情況並不理想,但我們還是繼續前行。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外柵欄。 但我們的快樂是短暫的。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和實際基地之間的山上有聚光燈。 我們可以聽到收音機裡互相交談的聲音。 這確實不足為奇。 警察擁有很多監視權力,Pine Gap 的權力更大。 但可能他們也不需要。 他們可能只是期望我們會再次嘗試進入並一直在等我們。
不管怎樣,我們到達山頂、打開儀器並在基地的視野中進行哀歌的計劃看起來很不穩定。 新計劃是盡可能快地進行,希望我們能在被捕之前表演一些作品。 我們翻過柵欄。
正如那天晚上我被委派的那樣,我的角色是攝影師。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我配備了手機攝像頭和用於照明的頭燈。 我本來希望能有一點時間來拍攝正確的照片。 這看起來不太可能,當我們強行上山時,我打開電話,把手電筒放在頭上。
我們已經爬到半山腰了,令人驚訝的是,警察似乎還沒有發現我們。 但瑪格麗特已經筋疲力盡了。 她從琴盒中取出中提琴。 我低聲/喊叫弗朗茨回來拿他的吉他。 奇蹟般的是,樂器都調準了。 當比賽開始時,我用手電筒試圖拍照,我們的比賽結束了。 警察現在正來抓我們。
請注意,我們仍在移動,與他們賽跑到山頂,那裡的松峽就在我們面前。 我們的哀悼變成了遊行——吉姆拿著一張伊拉克戰爭中死去的孩子的照片,弗蘭茲彈著吉他,蒂姆拿著他的擴音器,瑪格麗特拉著中提琴。 儘管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快速走上一座崎嶇不平的山坡,而我唯一的光源就是頭燈發出的可憐的光束,但我還是試圖將這一切都記錄在鏡頭中。 可以說,最終的鏡頭並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知道我們永遠無法拿回手機或存儲卡,所以我的重點是確保它能夠上傳。 所以我會拍攝一些然後點擊上傳按鈕。
練習過的哀歌慢慢地開始,伴隨著一段兩音符的輓歌即興演奏。 從那裡開始,隨著一些令人驚嘆的中提琴演奏,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但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到達那裡。 警察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身邊。 他們繞過音樂家,喊道“他在直播!” 並徑直向我走來。 當時是凌晨 4 點,出於明顯的原因,我們的廣播沒有提前做廣告。 但很高興知道至少有一個人現場觀看了它。 我逃離了警察,仍然試圖拍攝並點擊“上傳”按鈕。 也許這為我贏得了幾秒鐘的時間,但僅此而已。 當我徒勞地躲開時,一名警察將我按倒在堅硬的地面上。 另一個立即落在我身上,將手機從我手中奪走。 他們把我的手臂扭回來,用繩子盡可能地把它們綁在一起。 他們每隻胳膊上各抓著一個警察,把我拖到了山頂。 這幾乎不是警察最糟糕的待遇,但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當我到達山頂時,我看到我的同伴都坐在周圍。 顯然他們是被允許暢通無阻地走到山頂的,而且沒有人對他們下手!

在北領地,警車的後部只是籠子。 這樣做我很確定可以阻止警察在炎熱的天氣裡把人煮死(就像2008年的沃德先生那樣),但在冬天的沙漠之夜,返回愛麗絲的半小時旅程會非常寒冷。 尤其是弗蘭茨,由於某種原因,他的毛衣被警察脫掉了。 幸運的是,我和蒂姆現在已經把可笑的鋁箔毯子拿掉了,弗朗茲用它裹住了他顫抖的身體。
在看守所的經歷很正常——睡覺,被叫醒去接受采訪,在採訪中你拒絕說什麼,被提供早餐(我們的飲食要求是否改變了——蒂姆是唯一的肉食者,把火腿從每個人的三明治中去掉了) ;弗蘭茨是素食主義者,他的三明治換成了額外的水果),無聊。 比被鎖在牢房裡更糟糕的是被鎖在牢房裡,電視開到最大音量,儘管我們確實在某一時刻從觀看人們在“Wipeout”中傷害自己中獲得了一些樂趣。 中午時分,我們被叫去法庭,我們認為這將是一次相當例行的出庭。
在這一點上我應該指出,我們沒有被指控因抗議活動而受到任何常見的即決犯罪。 Pine Gap 有自己的法律——《國防(特殊承諾)法》。 根據該法,非法侵入罪最高可判處七年監禁。 拍照又是七件事。 該法律在歷史上只使用過一次(儘管很多人以前都曾走過松峽)——那是在包括我們自己的吉姆·道林和瑪格麗特在內的四人小組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公民檢查”之後。 2005年,他們被判有罪並被罰款,但當檢方對判決提出上訴時(他們認為四人應該入獄),高等法院實際上駁回了最初的指控。 法院表示,該法律是針對國防設施的; 由於拒絕提供任何證據證明 Pine Gap 的實際用途,法院未能確定 Pine Gap 是否確實是與澳大利亞國防有關的設施。
作為回應,政府於 2008 年修改了法律,這樣爭論就不能再被使用。 整個過程確實有點可疑。 但這並不是這項法律唯一不尋常的地方。 由於這些懲罰極其嚴厲,未經聯邦總檢察長明確同意,你實際上不能對使用該法案的人提出指控。 在這種情況下,喬治·布蘭迪斯顯然沒有接聽電話。 所以警察已經告訴我們他們不能起訴我們並且會尋求休庭。 這對我們來說沒什麼問題,我們只是想出庭一次。 但後來,當我們坐在法院後面的拘留室時,事情開始變得有點瘋狂。
那天在愛麗斯泉的值班律師恰好是一位老活動人士,他在上次侵入松峽時認識了我們的一些船員。 當我們坐在拘留室時,他走進來告訴我們,他聽說檢方反對保釋。 如果他們成功了,這將意味著我們將被關押在愛麗絲泉的監獄裡,至少在他們得到喬治·布蘭迪斯的簽名之前是這樣。 這實際上也是史無前例的——通常只有那些被認為有逃跑風險或對社會構成危險的人才會拒絕保釋。
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並同意在地方法官面前反駁這一點應該不會太難。 不過,我們還有另一個驚喜。 當到了上法庭的時間時,我們並沒有被叫到一起。 只有一個人被帶出牢房並上法庭——弗朗茲。 公平地說,弗蘭茨是按字母順序排在第一位的。 但他也是最年輕的(19 歲),而且根本沒有法庭經驗。 現在他必須獨自面對敵意的起訴。 顯然,在法庭上,我們的朋友值班律師起身(在法庭禮儀中不按順序)說,單獨給弗蘭茲打電話是不公正的。 在牢房裡,我們給了他瘋狂的法律指示——“引用保釋推定!” 弗朗茨離開了牢房,我們其他人緊張地坐著。
當警衛傳喚我和吉姆時,他還沒有回來。 我們不確定會發生什麼,但這絕對不是我們會出庭並被告知指控被撤銷。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當我們在牢房裡時,戴諾·特里格法官一直在與檢方就《國防(特殊承諾)法案》進行爭論。 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報導,特里格稱該法律是“毫無意義的立法”。 未經總檢察長同意,我們不能被指控。 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所以我們受到了不正當指控,現在可以自由離開了。
法庭外,一大群支持者歡呼雀躍。 還有媒體攝像機。 我們出來了,對著鏡頭聊了一會兒。 弗蘭茨和瑪格麗特不間斷地演奏著他們的松峽輓歌。 然後我們坐下來放鬆一下。 這真是瘋狂的幾天。
瘋狂還沒有完全結束。 除了媒體(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無休無止的工作之外,籠罩在我們面前的是警察獲得批准並回來逮捕我們的前景。 隨著周末的臨近和法庭的休庭,我們預計會被拘留幾天——可能會更長。 我們的計劃是在兩天內離開小鎮,讓每個人都回到昆士蘭的日常生活。 我們決定前往城外的一處房產,並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保持低調。
與此同時,在愛麗絲泉,我高中時最好的朋友之一正在看新聞,並在法庭外看到我。 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繫了,但並不是每天都會有老朋友來到紅色中心——所以喬爾(我的朋友)知道抗議營地的位置,就前往那裡打招呼。
在相當不尋常的幾周中,這可能是整個故事中最奇怪的部分。 因為當喬爾出現在營地看望他的老朋友時,他發現只有一群活動人士以為警察會追捕我,而不是打算幫助搜查。 因此,當鄉村男孩/足球運動員/鋼鐵推銷員喬爾走到幾個人面前詢問我的下落時,他得到的只是人們說他們從未聽說過安迪·潘恩。 他拿出手機,給他們看了新聞裡我的照片。 他們聳聳肩。
最終,有人拿走了他的電話號碼並發送給我。 在試圖向我有些困惑的朋友解釋為什麼他很難接近我之後,我很高興能追上他。 現在是我們在愛麗絲的最後一天,所以在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後,我回到了我住過的合租屋並在那裡告別。 關於“結束戰爭”的 IPAN 會議正在進行,但在疲憊不堪的幾週後,我放棄了會議,而是在擁擠的托德酒店觀看了西部鬥牛犬隊贏得 AFL 旗幟。 夜晚以燭光“和平遊行”從瞭望台穿過城鎮結束。 在那裡(在我不可思議地隨機遇到了另一位老朋友之後),我們向老朋友、新朋友、同志、瘋狂的嬉皮士和愛麗斯泉鎮做了最後的告別。 我們鑽進麵包車,駛向沙漠遙遠的地平線。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 經過 40 個小時的連續輪換司機後,我們回到布里斯班,正好趕上參加團結一致的反 Pine Gap 行動。 幾個月後,喬治·布蘭迪斯終於抽出時間檢查他的語音信箱並簽署了備忘錄。 我們通過郵件收到了指控,並將於 XNUMX 月返回沙漠,證明那些在戰爭中殺戮和破壞的人,而不是那些抵抗戰爭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 努力創造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的漫長冒險的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