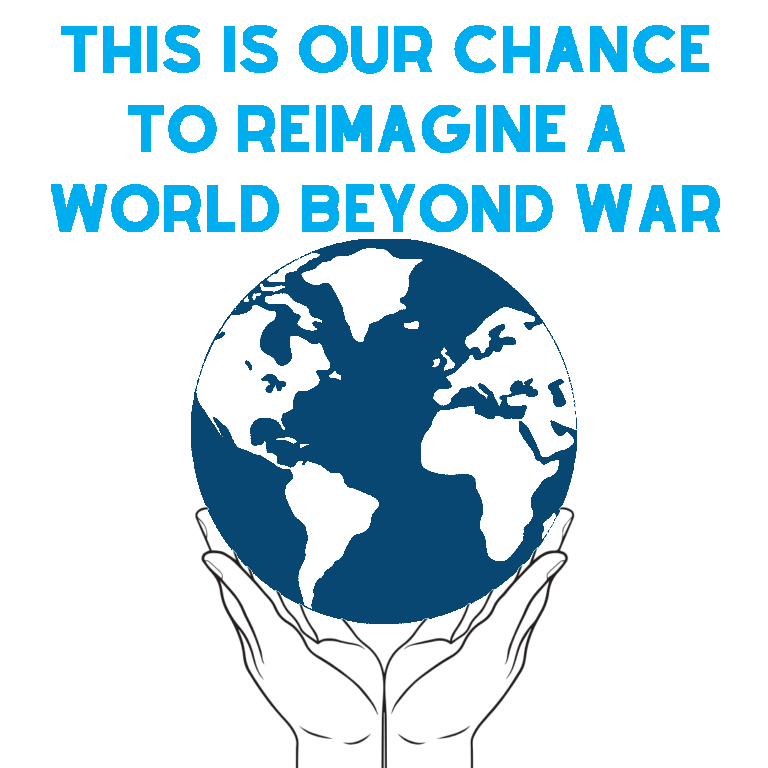作者:Jeffrey St. Clair – Alexander Cockburn,8 年 2017 月 XNUMX 日, 反擊.

慘淡的事實是,對中央情報局及其起源組織的活動進行仔細審查就會發現,中央情報局非常關注行為控制、洗腦以及對不知情的對象(包括宗教派別、種族)進行秘密醫學和心理實驗技術的發展。少數民族、囚犯、精神病人、士兵和絕症患者。 這些活動的基本原理、技術以及所選擇的人類受試者都顯示出與納粹實驗驚人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處。
當我們追溯美國情報官員為獲取納粹實驗記錄所做的堅定且常常成功的努力時,這種相似性就變得不那麼令人驚訝了,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自己招募納粹研究人員並讓他們工作,將實驗室從德皇達豪轉移過來。威廉研究所、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埃奇伍德兵工廠、德特里克堡、亨茨維爾空軍基地、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華盛頓大學。
1944 年 10,000 月的諾曼底登陸期間,當盟軍橫渡英吉利海峽時,大約 XNUMX 名被稱為“T 部隊”的情報官員緊隨先遣營後方。 他們的任務:抓獲軍火專家、技術人員、德國科學家及其研究材料,以及曾與納粹合作的法國科學家。 很快,大量此類科學家被抓起來並安置在一個名為“垃圾箱”的拘留營中。 在最初的任務計劃中,一個主要因素是認為德國的軍事裝備——坦克、噴氣式飛機、火箭等——技術優越,並且可以迅速向被俘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匯報情況,以便盟軍追捕被俘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向上。
隨後,1944 年 XNUMX 月,戰略情報局負責人比爾·多諾萬 (Bill Donovan) 和戰略情報局駐瑞士歐洲情報部門負責人艾倫·杜勒斯 (Allen Dulles) 強烈敦促羅斯福批准一項計劃,允許納粹情報官員、科學家和實業家“獲得許可”戰後進入美國並將其收入存入美國銀行等。” 羅斯福迅速拒絕了這一提議,他說:“我們預計,急於挽救自己生命和財產的德國人數量將迅速增加。 其中可能有些人應該因戰爭罪受到適當審判,或者至少因積極參與納粹活動而被捕。 即使有你提到的必要控制措施,我也不准備授權提供擔保。”
但總統的否決權在製定之際就已經是一紙空文。 陰雲行動確實在 1945 年 350 月開始,經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將 2 名德國科學家帶入美國,其中包括沃納·馮·布勞恩 (Werner Von Braun) 和他的 VXNUMX 火箭團隊、化學武器設計師以及火砲和潛艇工程師。 理論上曾有一些禁止輸入納粹分子的禁令,但這就像羅斯福的法令一樣空洞。 陰雲密布的貨物包括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和黨衛軍軍官,如馮·布勞恩、赫伯特·阿克斯特博士、阿瑟·魯道夫博士和喬治·里奇基。
馮·布勞恩的團隊使用了來自多拉 (Dora) 集中營的奴隸勞工,並在米特爾沃克 (Mittelwerk) 建築群中將囚犯活活折磨致死:超過 20,000 人因疲憊和飢餓而死亡。 監督奴隸主的是里奇基。 為了報復導彈工廠的破壞活動——囚犯們會在電氣設備上撒尿,導致嚴重的故障——里奇基會把十二個人一次吊在工廠的起重機上,並用木棍塞進他們的嘴里以阻止他們的哭聲。 在多拉集中營,他認為兒童是無用的嘴巴,並指示黨衛軍看守用棍棒打死他們,他們也這麼做了。
這一記錄並沒有阻止里奇基迅速調往美國,他被部署在俄亥俄州代頓附近的陸軍航空兵基地賴特機場。 里奇基開始負責監督其他數十名納粹分子的安全,這些納粹分子現在正在美國進行研究。 他還負責翻譯 Mittelwerk 工廠的所有記錄。 因此,他有機會並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個機會,銷毀任何對他的同事和他自己不利的材料。
到 1947 年,在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的刺激下,公眾感到足夠不安,要求對里奇基和其他一些人進行形式上的戰爭罪審判。 里奇基被送回西德,並接受了由美國陸軍監督的秘密審判,美國陸軍有充分的理由證明里奇基無罪,因為定罪將揭露現在在美國的整個 Mittelwerk 團隊都是使用奴隸制和酷刑的同謀以及殺害戰俘,因此也犯有戰爭罪。 因此,軍隊扣留了目前在美國的記錄,並阻止對代頓的馮·布勞恩和其他人進行任何審訊,從而破壞了對里奇基的審判:里奇基被無罪釋放。 然而,由於一些審判材料涉及魯道夫、馮·布勞恩和沃爾特·多恩伯格,整個記錄被保密並保密了四十年,從而埋葬了可能將整個火箭隊送上絞刑架的證據。
美國陸軍高級軍官知道真相。 最初,招募德國戰犯被認為是持續對日戰爭的必要條件。 後來,道德辯護採取了援引“智力賠償”的形式,或者正如參謀長聯席會議所說,“對我們希望利用其持續智力生產力的選定稀有人才的一種剝削形式”。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小組對這種令人厭惡的姿態表示贊同,該小組採取了學術立場,認為德國科學家通過成為“納粹化政治體中的一個不從眾的島嶼”,以某種方式逃避了納粹的蔓延,馮·布勞恩的聲明稱,里奇基和其他奴隸司機一定深感感激。
到 1946 年,基於冷戰戰略的基本原理變得更加重要。 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需要納粹分子,而他們的能力當然必須不讓蘇聯人知道。 1946 年 1,000 月,哈里·杜魯門總統批准了受杜勒斯啟發的回形針項目,其任務是將不少於 XNUMX 名納粹科學家帶到美國。 其中有許多戰爭中最卑鄙的罪犯:有來自達豪集中營的醫生,他們通過對囚犯進行高海拔測試來殺死他們,他們將受害者冷凍起來並給他們大量的鹽水來研究溺水的過程。 其中包括庫爾特·布洛姆(Kurt Blome)等化學武器工程師,他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囚犯身上測試過沙林神經毒氣。 有些醫生在拉文斯布呂克俘虜了女俘虜,用壞疽培養物、鋸末、芥子氣和玻璃填充她們的傷口,然後將她們縫合,並用一定劑量的磺胺藥物治療,同時給其他人計時,看看需要多長時間,從而造成戰場創傷。讓他們發展出致命的壞疽病例。
回形針招募計劃的目標包括赫爾曼·貝克爾-弗雷森和康拉德·謝弗,他們是《海上緊急情況下的口渴和解渴》研究的作者。 該研究的目的是想出一些方法來延長在水上墜落的飛行員的生存時間。 為此,兩位科學家要求海因里希·希姆萊從黨衛軍首領的集中營網絡中提供“四十名健康的測試對象”,科學家們之間唯一的爭論是研究受害者應該是猶太人、吉普賽人還是共產黨人。 實驗在達豪進行。 這些囚犯大部分是猶太人,人們通過管子將鹽水灌入喉嚨。 其他人則將鹽水直接注射到靜脈中。 一半的受試者服用了一種名為“berkatit”的藥物,這種藥物應該能讓鹽水變得更可口,儘管兩位科學家都懷疑,“berkatit”本身會在兩週內證明具有致命的毒性。 他們是正確的。 在測試過程中,醫生使用長針提取肝組織。 沒有給予麻醉劑。 所有研究對象均死亡。 Becker-Freyseng 和 Schaeffer 都獲得了 Paperclip 的長期合同; 謝弗最終來到了德克薩斯州,在那裡他繼續研究“口渴和鹽水淡化”。
貝克爾-弗雷森負責為美國空軍編輯由他的納粹同僚進行的大量航空研究。 此時他已被追踪並在紐倫堡接受審判。 這部名為《德國航空醫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多卷本著作最終由美國空軍出版,附有貝克爾-弗賴森在紐倫堡牢房中撰寫的簡介。 該書忽略了研究中的人類受害者,並稱讚納粹科學家是在第三帝國的束縛下工作的“具有自由和學術品格”的真誠和可敬的人。
他們的一位傑出同事是西格蒙德·拉舍爾博士(Dr. Sigmund Rascher),他也被派往達豪集中營。 1941 年,拉舍爾告訴希姆萊,迫切需要對人體進行高海拔實驗。 拉舍爾在威廉皇帝研究所任職期間開發了一種特殊的低壓室,他請求希姆萊允許將“兩到三名職業罪犯”交付給他,這是納粹對猶太人、俄羅斯戰俘和成員的委婉說法。波蘭地下抵抗組織。 希姆萊很快同意了,拉舍爾的實驗在一個月內就開始了。
Rascher 的受害者被鎖在他的低壓艙內,該艙模擬了高達 68,000 英尺的海拔。 八十隻人類豚鼠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被關在室內半小時後死亡。 其他數十人在半昏迷狀態下被拖出房間,並立即淹死在冰水桶中。 拉舍爾迅速切開他們的頭部,檢查大腦中有多少血管因空氣栓塞而破裂。 拉舍爾拍攝了這些實驗和屍檢,並將錄像連同他細緻的筆記一起發回給希姆萊。 拉舍爾寫道:“一些實驗給男人的頭部施加瞭如此大的壓力,以至於他們會發瘋並拔掉頭髮以減輕這種壓力。” “他們會用手撕扯自己的頭和臉,並尖叫,以減輕耳膜上的壓力。” 拉舍爾的記錄被美國情報人員收集並交給空軍。
美國情報官員對德魯·皮爾遜等人的批評表示蔑視。 JOIA 負責人 Bosquet Wev 將科學家們的納粹過去斥為“微不足道的細節”; 繼續譴責他們為希特勒和希姆萊所做的工作簡直就是“死馬當活馬醫”。 韋夫利用美國對斯大林在歐洲意圖的擔憂,認為將納粹科學家留在德國“對這個國家構成的安全威脅,比他們可能擁有的任何前納粹隸屬關係,甚至是他們可能仍然擁有的納粹同情心,都要大得多。”
Wev 的一位同事、G-2 開發部門負責人 Montie Cone 上校也表達了類似的實用主義。 “從軍事角度來看,我們知道這些人對我們來說非常寶貴,”科恩說。 “想想我們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了什麼——我們所有的衛星、噴氣式飛機、火箭,幾乎所有其他東西。”
美國情報人員對他們的任務如此著迷,以至於他們不遺餘力地保護新兵免受美國司法部刑事調查人員的侵害。 其中一個更卑鄙的案件是納粹航空研究員埃米爾·薩爾蒙的案件,他在戰爭期間幫助放火燒毀了一座擠滿猶太婦女和兒童的猶太教堂。 薩蒙在被德國去納粹化法庭定罪後,被美國官員庇護在俄亥俄州賴特空軍基地。
二戰結束後,納粹並不是美國情報人員尋找的唯一科學家。 在日本,美國陸軍僱傭了日本皇軍生物戰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博士。 石井博士針對中國和盟軍部署了多種生物和化學製劑,還在滿洲經營著一個大型研究中心,在那裡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戰俘進行了生物武器實驗。 石井讓囚犯感染破傷風; 給他們帶傷寒的西紅柿; 出現感染鼠疫的跳蚤; 感染梅毒的婦女; 並在數十名綁在木樁上的戰俘身上引爆炸藥。 除其他暴行外,石井的記錄顯示他經常對活體受害者進行“屍檢”。 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促成的一項協議中,石井向美國陸軍移交了 10,000 多頁的“研究成果”,避免了因戰爭罪而受到起訴,並受邀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演講。 德特里克是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附近的美國陸軍生物武器研究中心。
根據回形針條款,不僅戰時盟友之間存在激烈競爭,美國各軍種之間也存在激烈競爭——這始終是最野蠻的戰斗形式。 柯蒂斯·李梅認為他新組建的美國空軍肯定會導致海軍實際上的滅亡,並認為如果他能夠招募盡可能多的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一過程將會加快。 就美國海軍而言,它同樣渴望抓捕戰犯。 第一批被海軍救起的人是一位名叫西奧多·本辛格的納粹科學家。 本辛格是戰場創傷方面的專家,他在二戰末期通過人體爆炸實驗獲得了專業知識。 本辛格最終獲得了一份利潤豐厚的政府合同,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擔任研究員。
通過其在歐洲的技術任務,海軍還熱衷於追尋納粹對審訊技術的最先進研究。 海軍情報官員很快就發現了納粹關於吐真劑的研究論文,這項研究是由庫爾特·普洛特納博士在達豪集中營進行的。 普洛特納給猶太和俄羅斯囚犯服用高劑量的麥斯卡林,並觀察他們表現出精神分裂的行為。 囚犯們開始公開談論他們對德國俘虜的仇恨,並對他們的心理構成做出坦白陳述。
美國情報官員對普洛特納博士的報告產生了職業興趣。 曼哈頓計劃的戰略情報局、海軍情報和安全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在對所謂的 TD(即“真相藥物”)進行調查。 正如第 5 章中 OSS 官員喬治·亨特·懷特 (George Hunter White) 在黑手黨奧古斯托·德爾·格拉西奧 (Mafioso Augusto Del Gracio) 上使用 THC 的描述中所回憶的那樣,他們從 1942 年開始就開始試驗 TD。第一批受試者中的一些人是曼哈頓計劃的工作人員。 曼哈頓計劃中的四氫大麻酚劑量通過多種方式施用給目標,將液體四氫大麻酚溶液注入食物和飲料中,或浸入紙巾中。 曼哈頓安全團隊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興奮地報告說:“TD 似乎放鬆了所有抑制,並削弱了控制個人判斷力和謹慎性的大腦區域。” “它強調感官並凸顯個人的任何強烈特徵。”
但是有一個問題。 四氫大麻酚的劑量使受試者嘔吐,審訊者永遠無法讓科學家透露任何信息,即使藥物濃度額外。
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在閱讀普洛特納博士的報告後發現,他在使用麥斯卡林作為言語甚至真相誘導藥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審訊者能夠“在巧妙地提出問題時從受審者中提取出最私密的秘密”。 普洛特納還報告了麥斯卡林作為行為改變或精神控製劑的潛力的研究。
鮑里斯·帕什對這一信息特別感興趣,他是中央情報局早期角色中最險惡的人物之一。 帕什是一名移居美國的俄羅斯移民,經歷了蘇聯誕生時的革命歲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最終在戰略情報局工作,負責監督曼哈頓計劃的安全,除其他活動外,他還監督了對羅伯特·奧本海默的調查,並在這位著名原子科學家被懷疑幫助洩露秘密時擔任主要審訊者到蘇聯。
帕什以安全主管的身份監督了 OSS 官員喬治·亨特·懷特 (George Hunter White) 對曼哈頓計劃科學家使用 THC 的情況。 1944 年,帕什被多諾萬任命為“阿爾索斯任務”的負責人,該任務旨在挖取參與原子、化學和生物武器研究的德國科學家。 帕什在一位戰前老朋友、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尤金·馮·哈根博士的家裡開設了商店,許多納粹科學家都曾在該大學任教。 帕什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休假時認識了馮·哈根,當時他正在研究熱帶病毒。 1930 世紀 XNUMX 年代末,馮·哈根返回德國後,他和庫爾特·布洛姆 (Kurt Blome) 成為納粹生物武器部門的聯合負責人。 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馮·哈根讓納茨韋勒集中營的猶太囚犯感染了斑疹熱等疾病。 帕什並沒有被老朋友的戰時活動所嚇倒,他立即將馮·哈根納入回形針計劃,在那裡他為美國政府工作了五年,提供細菌武器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
馮·哈根讓帕什與他的前同事布洛姆取得了聯繫,布洛姆也很快加入了回形針項目。 當布洛姆因戰爭醫療罪被捕並在紐倫堡受審時,有一個不方便的間歇,其中包括故意讓數百名波蘭地下囚犯感染結核病和黑死病。 但幸運的是,對於這位納粹科學家來說,美國陸軍情報局和戰略情報局扣留了他們通過審訊獲得的有罪文件。 這些證據不僅證明了布洛姆的罪行,還證明了他在建造德國生化武器實驗室以測試盟軍使用的化學和生物武器方面的監督作用。 布洛姆下了車。
1954 年,布洛姆被無罪釋放兩個月後,美國情報官員前往德國採訪他。 在給上級的一份備忘錄中,HW Batchelor 描述了這次朝聖的目的:“我們在德國有朋友,科學界的朋友,這是一個很高興與他們見面討論我們的各種問題的機會。” 在會議上,布洛姆向巴徹勒提供了一份戰爭期間為他工作的生物武器研究人員名單,並討論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究的有希望的新途徑。 布洛姆很快就以每年 6,000 美元的價格簽訂了一份新的回形針合同,並飛往美國,在華盛頓特區郊外的一個軍事基地金營 (Camp King) 上任。 1951 年,馮·哈根被法國當局逮捕。 儘管美國情報部門的保護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這位醫生還是被判犯有戰爭罪並被判處二十年監禁。
從回形針任務中,帕什現在在新生的中央情報局工作,後來成為項目部門/7的負責人,他對審訊技術的持續興趣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Program Branch/7 的任務直到 1976 年參議員弗蘭克·丘奇 (Frank Church) 的聽證會上才被曝光,它負責中央情報局綁架、審訊和殺害可疑的中央情報局雙重間諜。 帕什仔細研究了達豪納粹醫生的工作,尋找最有效的信息提取方法的有用線索,包括言語誘導藥物、電擊、催眠和精神外科手術。 在帕什領導 PB/7 期間,中央情報局開始向藍鳥計劃投入資金,旨在復制和擴展達豪研究中心的研究。 但中央情報局沒有使用麥司卡林,而是轉向了由瑞士化學家阿爾伯特·霍夫曼開發的LSD。
中央情報局的第一次 LSD 藍鳥測試對 150 名受試者進行了測試,其中大多數是黑人,正如中央情報局達豪納粹醫生的精神病學家模擬器所指出的那樣,“心態不太高”。 受試者被告知他們正在服用一種新藥。 用中央情報局藍鳥備忘錄的話說,中央情報局的醫生們清楚地知道LSD實驗會誘發精神分裂症,並向他們保證“不會發生任何嚴重的”或危險的事情。 中央情報局的醫生給這十二人服用了 XNUMX 微克的 LSD,然後對他們進行了敵意的審訊。
經過這些試運行後,中央情報局和美國陸軍從 1949 年開始在馬里蘭州埃奇伍德化學兵工廠進行廣泛的測試,並持續到接下來的十年。 7,000多名美國士兵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了這項醫學實驗的對象。 這些男子將被命令戴著氧氣面罩騎自行車運動,面罩上噴灑了各種致幻藥物,包括 LSD、麥司卡林、BZ(一種致幻劑)和 SNA(sernyl,PCP 的親戚,在街道如天使之塵)。 這項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誘導一種完全失憶的狀態。 在幾個受試者的情況下實現了這一目標。 參加實驗的一千多名士兵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困擾和癲癇症:數十人試圖自殺。
勞埃德·甘布爾(Lloyd Gambl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應徵入伍的黑人。 1957 年,甘布爾受邀參加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的藥物測試計劃。 甘布爾被引導相信他正在測試新的軍裝。 作為參加該計劃的誘因,他獲得了延長假期、私人居住區和更頻繁的夫妻探訪。 三個星期以來,甘布爾穿上又脫下不同類型的製服,據他回憶,每天在這樣的努力中,他都會喝兩到三杯水狀液體,這實際上是迷幻藥。 甘布爾出現了可怕的幻覺並試圖自殺。 大約十九年後,當教會聽證會披露該計劃的存在時,他了解到了真相。 即便如此,國防部仍否認甘布爾參與其中,直到一張舊的國防部公共關係照片浮出水面時,掩蓋才被瓦解,照片中自豪地標明甘布爾和其他十幾個人“自願參與一項符合最高國家安全利益的項目”。 ”。
美國情報機構準備對未知對象進行實驗的例子,沒有比國家安全機構涉足輻射影響研究更生動的了。 共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實驗。 其中一項涉及數千名美國軍事人員和平民,他們直接暴露於美國西南部和南太平洋核試驗的放射性塵埃中。 許多人都聽說過黑人男子是聯邦資助的梅毒研究的受害者,這些研究長達四十年,其中一些受害者被給予安慰劑,以便醫生能夠監測疾病的進展。 就馬紹爾群島人而言,美國科學家首先設計了 H 測試——其威力是廣島原子彈的一千倍——然後未能警告附近朗格拉普環礁的居民輻射的危險,然後,精確地納粹科學家們平靜地觀察著他們的表現(這並不奇怪,因為被中央情報局官員鮑里斯·帕什救出的參與德國輻射實驗的納粹老兵現在已經加入了美國團隊)。
最初,馬紹爾群島居民被允許在環礁上停留兩天,接受輻射。 然後他們就被疏散了。 兩年後,原子能委員會生物學和醫學委員會主席 G. Faill 博士要求將朗格拉普島民送回環礁,“對這些人的影響進行有用的基因研究”。 他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1953 年,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簽署了一項指令,要求美國政府遵守紐倫堡醫學研究準則。 但該指令被列為絕密,其存在對研究人員、受試者和政策制定者保密了 XNUMX 年。 原子能委員會的 OG Haywood 上校簡潔地總結了這項政策,他將自己的指令正式化:“希望不要發布任何涉及人體實驗的文件。 這可能會對公眾產生不利影響或導致法律訴訟。 涵蓋此類實地工作的文件應保密。”
在這些被列為秘密的實地工作中,有五項不同的實驗由中央情報局、原子能委員會和國防部監督,涉及在未經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向至少十八人(主要是黑人和窮人)注射钚。 1948 年至 1952 年間,美國和加拿大城市上空有 2,000 次故意釋放放射性物質,以研究放射性粒子的沉降模式和衰變。 中央情報局和原子能委員會資助了數十項實驗,這些實驗通常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進行,對 XNUMX 多名不知情的人進行了輻射掃描。
埃爾默·艾倫的例子很典型。 1947 年,這位 36 歲的黑人鐵路工人因腿部疼痛前往芝加哥的一家醫院。 醫生診斷他的病顯然是骨癌。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他們給他的左腿注射了大劑量的钚。 第三天,醫生截掉了他的腿,並將其送到原子能委員會的生理學家那裡,研究钚是如何在組織中擴散的。 1973 年後,即 1947 年,他們將艾倫帶回芝加哥郊外的阿貢國家實驗室,在那裡對他進行了全身輻射掃描,然後採集了尿液、糞便和血液樣本,以評估他體內 XNUMX 年的钚殘留量。實驗。
1994 年,在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從事钚實驗的帕特里夏·杜賓 (Patricia Durbin) 回憶道:“我們一直在尋找患有某種絕症、即將接受截肢的人。 做這些事情並不是為了困擾人們或讓他們生病或痛苦。 他們不是為了殺人而生的。 這樣做是為了獲取潛在有價值的信息。 事實上,他們被注射並提供了這些有價值的數據,這幾乎應該是一種紀念,而不是值得羞恥的事情。 我並不介意談論钚注射者,因為他們提供的信息很有價值。” 這個淚流滿面的敘述的唯一問題是,當埃爾默·艾倫因腿部疼痛去醫院時,他似乎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而且從未被告知對他的身體進行的研究。
1949 年,馬薩諸塞州費納德學校的智障男孩的家長被要求同意他們的孩子加入學校的“科學俱樂部”。 那些加入俱樂部的男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實驗對象,原子能委員會與貴格會燕麥公司合作給他們提供了放射性燕麥片。 研究人員想看看穀物中的化學防腐劑是否會阻止人體吸收維生素和礦物質,而放射性物質則充當示踪劑。 他們還想評估放射性物質對孩子們的影響。
美國政府模仿納粹的方法,進行秘密醫學實驗,尋找最脆弱和最受俘虜的受試者:智障者、絕症患者,以及毫不奇怪的囚犯。 1963年,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133名囚犯的陰囊和睾丸受到了600倫琴的輻射。 拍攝對象之一是哈羅德·畢博 (Harold Bibeau)。 如今,他是一名 55 歲的繪圖員,住在俄勒岡州特勞特代爾。 自 1994 年以來,Bibeau 一直在與美國能源部、俄勒岡懲戒部、巴特爾太平洋西北實驗室和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進行一場單人戰鬥。 因為他有前科,所以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得到太多滿足。
1963年,比博因殺害一名試圖對他進行性騷擾的男子而被定罪。 比博因故意殺人罪被判十二年徒刑。 在監獄裡時,另一名囚犯告訴他一個方法,可以讓他減刑並賺點小錢。 比博可以通過加入一個據稱由該州醫學院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管理的醫學研究項目來做到這一點。 比博說,雖然他確實簽署了一份參與該研究項目的協議,但他從未被告知這可能會對他的健康造成危險的後果。 事實證明,對比博和其他囚犯(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總共 133 名囚犯)進行的實驗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該研究涉及輻射對人類精子和性腺細胞發育的影響的研究。
Bibeau 和他的同事們受到了 650 拉德的輻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劑量。 如今,一張胸部 X 光檢查涉及約 1 拉德。 但這還不是全部。 比博說,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在監獄裡被多次注射其他藥物,但其性質他並不了解。 他接受了活組織檢查和其他手術。 他聲稱,出獄後,再也沒有人聯繫過他進行監控。
俄勒岡州的實驗是為原子能委員會進行的,中央情報局作為合作機構。 負責俄勒岡州測試的是卡爾·海勒博士。 但實際上,對比博和其他囚犯進行的 X 光檢查是由完全不合格的人(以其他監獄囚犯的形式)進行的。 Bibeau 沒有獲得任何減刑,他每月獲得 5 美元的報酬,每次睾丸活檢獲得 25 美元的報酬。 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監獄實驗中的許多囚犯都接受了輸精管切除術或手術閹割。 進行絕育手術的醫生告訴囚犯,絕育是必要的,以“防止輻射引起的突變體污染普通民眾”。
布魯克海文核實驗室的醫生維克多·邦德博士在為滅菌實驗辯護時說:“了解什麼劑量的輻射可以滅菌是很有用的。 了解不同劑量的輻射會對人類產生什麼影響是很有用的。” 邦德的一位同事、舊金山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約瑟夫·漢密爾頓博士更坦誠地說,輻射實驗(他曾協助監督)“有點像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風格”。
從 1960 年到 1971 年,辛辛那提大學的尤金·桑格博士和他的同事對 88 名黑人、窮人和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受試者進行了“全身輻射實驗”。 受試者受到 100 拉德的輻射——相當於 7,500 次胸部 X 光檢查。 這些實驗經常引起劇烈疼痛、嘔吐以及鼻子和耳朵流血。 除一名患者外,所有患者均死亡。 1970 世紀 XNUMX 年代中期,國會委員會發現桑格偽造了這些實驗的同意書。
1946 年至 1963 年間,超過 200,000 萬美國士兵被迫在太平洋和內華達州危險的近距離觀察大氣層核彈試驗。 其中一位參與者,一位名叫吉姆·奧康納 (Jim O'Connor) 的美國陸軍二等兵,在 1994 年回憶道:“有一個長得像人體模型的人,顯然是爬到了一個掩體後面。 他的手臂上纏著電線一樣的東西,臉上血跡斑斑。 我聞到了一股肉燒焦的味道。 我看到的旋轉攝像機正在變焦變焦變焦,而那個人一直試圖站起來。” 奧康納本人逃離了爆炸區域,但被原子能委員會巡邏隊接走,並接受了長時間的測試以測量他的暴露程度。 奧康納在 1994 年表示,自從接受測試以來,他經歷了許多健康問題。
1949 年 1970 月,在華盛頓州漢福德的核保留地,原子能委員會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放射性化學物質故意釋放。這次試驗沒有涉及核爆炸,而是釋放了數千居里的放射性物質。碘呈羽狀擴散,向南和向西延伸數百英里,最遠到達西雅圖、波特蘭和加利福尼亞州與俄勒岡州邊境,輻射了數十萬人。 當時,平民百姓並未對這項檢測產生警惕,直到 XNUMX 世紀 XNUMX 年代末才得知這一消息,儘管由於下風社區中出現大量甲狀腺癌,人們一直對此抱有懷疑。
1997 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發現,數百萬美國兒童接觸過高濃度的放射性碘,已知這些放射性碘會導致甲狀腺癌。 大部分暴露是由於飲用了受到 1951 年至 1962 年間進行的地面核試驗的放射性塵埃污染的牛奶。該研究所保守估計,這足以導致 50,000 例甲狀腺癌。 據估計,總輻射釋放量比 1986 年蘇聯切爾諾貝利反應堆爆炸釋放的輻射量還要多十倍。
1995 年,一個總統委員會開始調查人體輻射實驗,並要求中央情報局交出所有記錄。 該機構回應稱,“它沒有有關此類實驗的記錄或其他信息。” 中央情報局對這種粗暴的阻撓感到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是,1973 年,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退休前的最後一刻下令銷毀所有中央情報局人體實驗的記錄。 中央情報局監察長 1963 年的一份報告表明,十多年來,該機構一直致力於研究和開發能夠用於秘密行動以控制人類行為的化學、生物和放射性材料。 1963 年的報告接著說,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批准了各種形式的人體實驗作為“控制人類行為的途徑”,包括“輻射、電擊、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各個領域、筆跡學、騷擾研究和準軍事”。設備和材料。”
1975 年,監察長的報告以經過嚴格編輯的形式出現在國會聽證會上。 至今仍屬於機密。 1976 年,中央情報局告訴教會委員會,它從未使用過輻射。 但這一說法在 1991 年被削弱了,當時該機構的文件被發現。
朝鮮薊計劃。 中央情報局對朝鮮薊的總結稱,“除了催眠、化學和精神病學研究之外,還探索了以下領域……其他物理表現,包括熱、冷、大氣壓力、輻射。”
1994 年,由能源部部長黑澤爾·奧利裡 (Hazel O'Leary) 成立的總統委員會跟踪了這些證據並得出結論,中央情報局確實在探索輻射作為防禦性和進攻性使用洗腦和其他審訊技術的可能性。 該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引用了中央情報局的記錄,顯示該機構在 1950 世紀 1977 年代秘密資助了喬治敦大學醫院的側翼建設。 這裡將成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化學和生物項目研究的天堂。 中央情報局為此提供的資金轉給了管理 Geschickter 醫學研究基金的 Charles F. Geschickter 博士。 這位醫生是喬治敦大學的一名癌症研究人員,因進行高劑量輻射實驗而出名。 XNUMX 年,Geschickter 博士作證說,中央情報局支付了他的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和設備的費用,並密切監視了他的研究。
中央情報局是一系列跨機構政府人體實驗小組的主要參與者。 例如,三名中央情報局官員在國防部醫學科學委員會任職,這些官員也是原子戰醫學方面聯合小組的關鍵成員。 該政府委員會負責規劃、資助和審查大多數人體輻射實驗,包括在 1940 世紀 1950 年代和 XNUMX 年代進行的核試驗附近部署美軍。
中央情報局也是武裝部隊醫療情報組織的一部分,該組織成立於 1948 年,負責“從醫學科學角度來看的外國、原子、生物和化學情報”。 這次任務中最奇怪的一章是派遣一隊特工進行某種形式的搶奪屍體,他們試圖從屍體上收集組織和骨骼樣本,以確定核試驗後的放射性塵埃水平。 為此,他們在死者親屬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從約 1,500 具屍體上切下了組織。 原子能機構核心作用的進一步證據是它在聯合原子能情報委員會(外國核計劃情報交換所)中的主導作用。 中央情報局擔任科學情報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聯合醫學科學情報委員會的主席。 這兩個機構都為國防部規劃了輻射和人體實驗研究。
這絕不是該機構在活人實驗中發揮的全部作用。 如前所述,理查德·赫爾姆斯於 1973 年正式中止了中情局的此類工作,並下令銷毀所有記錄,稱他不希望中情局從事此類工作的同事“感到尷尬”。 至此,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結束了對貝克爾-弗賴森和布洛姆等納粹“科學家”的延長工作。
來源
兩本優秀但不公正地被忽視的書講述了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招募納粹科學家和戰爭技術人員的故事:湯姆·鮑爾的 回形針陰謀:追捕納粹科學家 和琳達·亨特的 秘密議程。 尤其是亨特的報導是一流的。 利用《信息自由法》,她打開了來自五角大樓、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數千頁文件,這些文件應該讓研究人員在未來幾年裡忙碌起來。 納粹醫生的實驗歷史很大程度上來自紐倫堡法庭的醫療案件審判記錄,亞歷山大·米切爾利希和弗雷德·米爾克的 臭名昭著的醫生,以及羅伯特·普羅克特 (Robert Proctor) 的可怕敘述 種族衛生。 珍妮·麥克德莫特的書中對美國政府對生物戰的研究進行了令人欽佩的描述, 殺戮之風.
對美國政府在開發和部署化學戰劑方面的作用的最佳描述仍然是西摩·赫什的書 化學和生物戰 從 1960 世紀 1994 年代末開始。 為了找出海灣戰爭綜合症的原因,參議員傑·洛克菲勒就美國政府的人體實驗舉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聽證會。 聽證會記錄為本章涉及中央情報局和美國陸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美國公民進行的實驗的部分提供了大部分信息。 關於原子能委員會和合作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進行的人體輻射測試的信息主要來自幾項 GAO 研究、能源部 XNUMX 年編制的大規模報告以及作者對四名钚和原子彈受害者的採訪。滅菌實驗。
本文改編自《Whiteout:中央情報局、毒品和新聞界》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