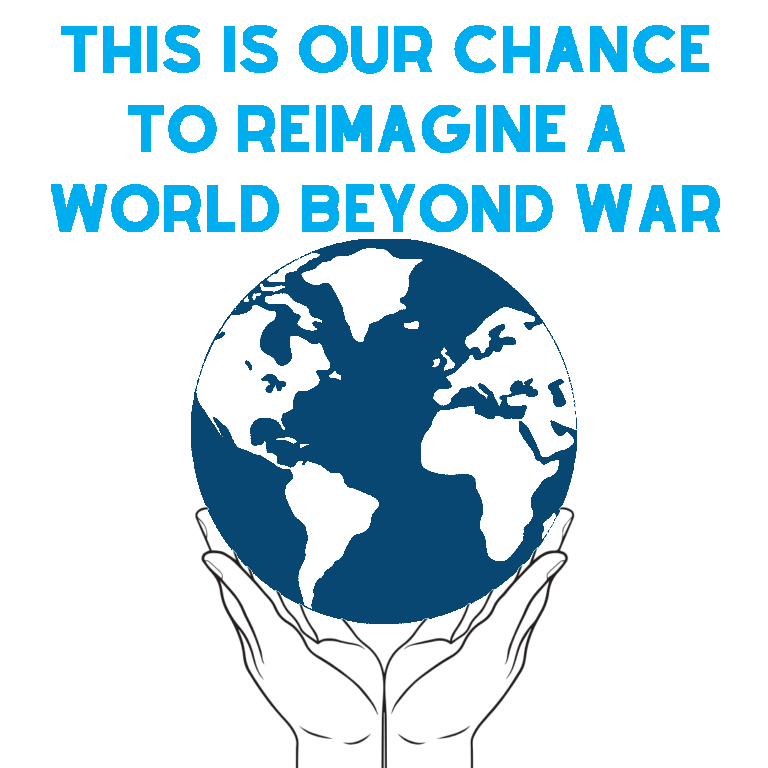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勇氣是生命給予和平的代價。”
— 阿米莉亞·埃爾哈特
畫肖像需要時間,急於求成。 我的規則是熱情但有耐心,留出時間思考,因為我努力在眼睛中獲得精確的閃光,就這樣彎曲嘴唇,並在鼻樑上塑造高光以適應其輪廓。
丹尼爾·黑爾,他的 肖像 我一直在畫的是一位空軍無人機舉報人,他出於良心而不得不發布機密文件,顯示近90% 的無人機暗殺受害者都是平民,無辜的人,是在他的幫助下被謀殺的。 他無法忍受這一點。 丹尼爾知道公佈這些材料會招致政府的憤怒。 他將根據《間諜法》被起訴,就像他是間諜一樣。 面臨數年監禁,現已因說出真相而被判處 45 個月監禁。 他說,比坐牢更讓他害怕的是不去質疑這些無人機謀殺案的誘惑。 他的軍事職責是保持沉默。 但什麼樣的人不會質疑他所負責的行為呢? 他的生命比被殺的人更有價值嗎? 他說:“我得到了答案,為了製止暴力的循環,我應該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另一個人的生命。”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對踩踏螞蟻毫不在意,長長的棕色和黑色的小螞蟻在偵察食物,其他螞蟻帶著麵包屑或其他昆蟲的碎片——蚱蜢的腿,蒼蠅的翅膀— —返回。 我不尊重他們作為生物,不認為他們是具有復雜社會組織的進化的奇蹟產物,不認為他們擁有與我一樣的存在權利。
他們對我壓倒性的力量毫不在意。
我的普遍文化觀念是,昆蟲是不好的,對人類有害,攜帶疾病或破壞我們的食物,或者只是令人毛骨悚然,它們會潛入我們的房子,用它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讓我們感到不安,我母親聲稱,它們會蜂擁而至,吃掉任何甜食,然後留下來。 、隱匿性疾病。 打碎一隻小昆蟲,即使不是正義的行為,至少也能讓世界變得更適合人類居住。 我從來沒有被告知他們生活在同一個生命網絡中,其中包括我和我的福利。 我沒有被教導要對它們的存在感到驚訝。 我自己也沒有直覺到這一點。 我沒有被教導要像螞蟻兄弟姐妹一樣問候他們。 對昆蟲報仇是合乎道德的,而對它們的感激則荒唐可笑。
我為什麼要考慮這個? 有一天我看了索尼婭·肯納貝克的紀錄片 國鳥 (2016) 關於三名無人機操作員舉報人,其中包括丹尼爾·黑爾 (Daniel Hale)。 在對成為美國無人機襲擊目標的阿富汗平民、一些倖存者、一些遇難者親屬以及一些致殘受害者的採訪中,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強烈的悲痛。 影片中無人機在向汽車、卡車、公共汽車、房屋和集會發射導彈之前所看到的畫面令人震驚。 不清晰,但有顆粒感,污跡,黑白相間,人們騎著或走著,從高處看去,被縮短得像笨拙的小昆蟲,根本不是人類,更像是螞蟻。
我們都知道,戰爭是由於我們不幸地有能力使敵人失去人性而引發的。 恐懼和憤怒、蔑視和宣傳使敵人淪為成群結隊的昆蟲,意圖咬、刺、殺死我們。 我們不太容易認識到的是,當我們正義地願意向他們使用可怕的、不分皂白的武器時,我們同樣也使自己失去了人性。 完全的人類能否為無人機襲擊辯護,駁回對眾多平民的謀殺,以消滅一個涉嫌對美國人造成傷害的人? 我八歲的時候,粉碎一隊只想養活自己的螞蟻,這又是多麼人性化的事呢?
美國人一直被灌輸這樣的觀念:攝像機的技術非常先進,操作員可以區分微笑和皺眉、AK-47 和拉哈布(傳統樂器)、男人和女人、八歲的孩子和女人。少年,有罪自不。 幾乎不。 運營商真的不知道。 他們的偏見也不允許他們知道。 在電影中我們聽到他們在猜測。 青少年是事實上的敵方戰鬥人員,兒童是兒童,但誰真正在乎呢? 或許,十二歲是什麼? 最好站在戰鬥者一邊。 它們都是螞蟻,正如我們常說的,歸根結底,被肢解的螞蟻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事實證明,無人機攝像頭唯一看到的就是螞蟻。
* * *
美國政府指控丹尼爾·黑爾竊取政府財產和機密信息,詳細說明了無人機襲擊造成的平民死亡程度。 政府認為,如果敵對或潛在敵對國家的人們知道我們願意為附帶謀殺辯護,他們可能會想要復仇,甚至覺得在道德上有義務實施報復。 我們的政府可能會進一步假設,公正的美國人可能也會同樣感到憤怒,並要求結束無人機暗殺。 用於對付丹尼爾·黑爾的《間諜法》不是道德法準則,而是將宣傳置於法律控制之下。 這也與美國的安全無關,除非讓很多人知道你正在實施可怕的不道德行為往往會降低一個人的安全性。 丹尼爾·黑爾發誓對美國無人機暴行的真實性質保密。
保密政策是一種自戀。 我們迫切希望尊重自己,並讓其他人尊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是誰,而是因為我們假裝自己是誰——傑出的、熱愛自由的、擁抱民主的、遵守法律的、住在山上豪宅里的善良的人們,他們必然拿著一根大棒為了所有人的利益。
因此,我們對反人類罪保密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國際法的影響——美國為自己逃避國際法的管轄。 這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免受對我們永恆善良的神話的攻擊。 我們的政府實行各種自戀,夾雜著憤世嫉俗和冷酷無情,其理念是,如果人們看不到你所做的事情,他們就會對你所說的做出無罪推論。 如果人們能夠習慣性地認為我們是善良的,那麼我們一定是善良的。
* * *
在繪畫時,我試圖理解丹尼爾·黑爾(Daniel Hale)和達內拉·弗雷澤(Darnella Frazier)之間的相似之處,達內拉·弗雷澤是一位年輕女子,她冷靜地拍攝了德里克·肖萬謀殺喬治·弗洛伊德的視頻。 沙文是國家權力的保護者和執行者。 多年來,該政權實施的種族主義暴力行為一直不受懲罰,因為國家本身就是由種族主義構成的。 謀殺有色人種並不是真正的犯罪。 無人機上的導彈就像國家權力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樣,殺死了像喬治·弗洛伊德這樣的平民,卻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在技術使平民能夠記錄國家在美國境內犯下的種族主義罪行之前,此類罪行實際上被分類,因為法院傾向於警察的虛假證詞。 因此,丹尼爾·黑爾試圖像達內拉·弗雷澤一樣,成為謀殺案的證人,但保密規則禁止他成為證人。 如果在喬治·弗洛伊德被殺後,四名警察讓所有證人宣誓保密,並聲稱這是受保護的警察事務,結果會怎樣呢? 如果警察搶走了達內拉的相機並將其砸碎或刪除了視頻或因監視警察事務而逮捕她怎麼辦? 此後,警察就成為默認的可信證人。 在黑爾的案例中,奧巴馬總統在電視上強烈宣稱美國非常謹慎,只會用無人機殺死目標恐怖分子。 沒有達內拉·丹尼爾·弗雷澤·黑爾,謊言就會變成真相。
令人惱火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對喬治·弗洛伊德被殺的不公正反應如此激烈,卻對美國無人機殺害無辜男女和兒童的視覺證據反應如此激烈,其方式只能被描述為同樣冷酷無情,甚至更加殘酷。惡毒。 阿拉伯人的生命不重要嗎? 或者這裡是否存在另一種自戀——喬治·弗洛伊德是我們部落的人,而阿富汗人不是。 同樣,儘管大多數人承認越南戰爭是美國國家的犯罪行為,但我們記得58,000名美國人在越南被殺,卻忽略了3至4萬越南人、老撾人和柬埔寨人。
* * *
我在為丹尼爾·黑爾作畫時看到了阿米莉亞·埃爾哈特的這句話:“勇氣是實現和平的代價。”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她正在談論在自身之外實現和平——人與人之間、社區之間、國家之間的和平。 但也許同樣重要的和平是通過有勇氣使自己的行為與良知和理想保持一致而與自己實現的和平。
做到這一點可能是有價值的生活中最困難和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一個試圖以這種方式調整自己的生活必須堅定地反對想要控制它的權力,將其打入沉默的群體中,接受權力習慣於日常暴力來維持自身及其利益的群體的一員。 。 這樣的生活承擔著我們所謂的沉重負擔。 這種負擔接受了堅持良心要求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這個負擔是我們的勝利,是我們最終的尊嚴,無論我們的壓迫者多麼強大,都無法從我們身上奪走。 這就是精緻的部分,賦予道德選擇光輝燦爛的勇氣。 精美的是一個人為真理所發出的光芒。 丹尼爾·黑爾(Daniel Hale)擔心不去質疑無人機政策的誘惑。 他擔心同謀是相反的負擔,會犧牲他的道德自主權和尊嚴。 權力認為你最大的恐懼就是讓自己受到它的擺佈。 (有趣的是,“仁慈”這個詞;權力因其願意無情而仍然是權力。)丹尼爾·黑爾(Daniel Hale)擔心自己無法擺脫無人機政策的殘酷不道德,比他被送進監獄更擔心。 通過讓自己容易受到權力的影響,他擊敗了權力。 那個負擔很精緻。
我不干畫聖人的事。 我喜歡我們所有人都容易犯錯,喜歡我們必須與自己、與我們的文化進行鬥爭,以獲得道德上的勝利。 但當一個人像丹尼爾·黑爾那樣行事,堅持自己的良心,藐視權力的意誌時,他就有幸擁有一定程度的純潔性。 如果我們願意支持他,幫助他承擔他的沉重負擔,這樣的祝福可以鼓舞我們所有人。 共同承擔這個重擔也是民主的希望。 政策研究所聯合創始人馬庫斯·拉斯金 (Marcus Raskin) 表示:“民主及其運作原則,即法治,需要一個立足的基礎。 那根基就是真理。 當政府撒謊,或者像我們的國家安全國家那樣構建謊言和自欺欺人時,那麼我們的官方結構就違背了民主憲政的基本前提。”
丹尼爾·黑爾加入空軍時無家可歸。 一個來自不和諧家庭的溫柔的年輕人。 軍隊為他提供了穩定、社區和使命。 它還要求他參與暴行。 還有保密性。 要求他道德自殺。 我在他的畫中刻下了他的一句話:
“在無人機戰爭中,有時被殺的十分之九是無辜的。 你必須犧牲一部分良心才能完成你的工作……但是我能做些什麼來應對我所犯下的不可否認的殘酷行為呢?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不去質疑的誘惑。 所以我聯繫了一位調查記者……並告訴他我有一些美國人民需要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