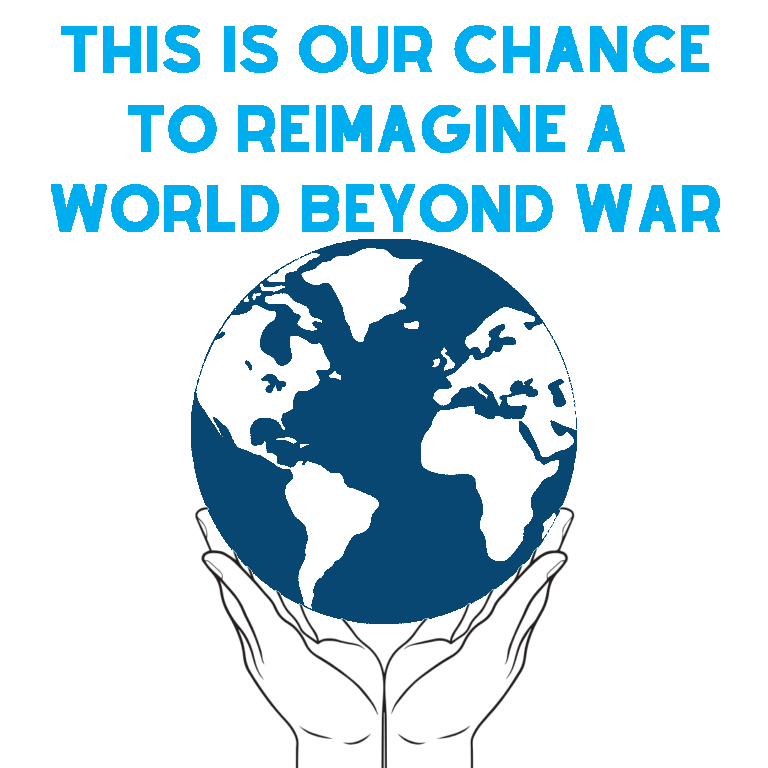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照片: 吉爾赫梅·喬菲利 / Flickr)
(照片: 吉爾赫梅·喬菲利 / Flickr)
堅守庫布奇沙漠防線
在內蒙古包頭,一百名昏昏沉沉的韓國大學生跌跌撞撞地走下火車,在明亮的陽光下眨著眼睛。 包頭距北京 14 小時火車車程,絕不是首爾年輕人的熱門目的地,但這也不是購物之旅。
一名身著亮綠色夾克的矮個子老人帶領著學生們穿過車站的人群,急忙向大家發號施令。 與學生們相比,他一點也不顯得疲倦; 他的笑容並未因旅途而受到影響。 他的名字叫權秉賢 (Kwon Byung-Hyun),是一名職業外交官,曾於 1998 年至 2001 年間擔任大韓民國駐華大使。雖然他的職責範圍曾經涵蓋貿易、旅遊、軍事和朝鮮等各個領域,但權大使卻找到了新的事業這需要他全神貫注。 74歲的他沒有時間去看望忙著打高爾夫球或沉迷於業餘愛好的同事。 權大使正在首爾的小辦公室裡打電話、寫信,以製定國際應對措施,應對中國沙漠的蔓延——或者他在這裡植樹。
權說話的語氣輕鬆又平易近人,但他一點也不隨和。 雖然他需要兩天時間才能從首爾山上的家到達久淵沙漠的前線,因為庫布奇沙漠不可避免地向東南方向移動,但他經常帶著熱情去旅行。
久淵地沙漠已經擴大,距北京以西僅450公里,是距離韓國最近的沙漠,是韓國大風吹來的黃塵的主要來源。 權先生於2001年創立了非政府組織“未來森林”,與中國密切合作防治荒漠化。 他將韓國和中國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通過一個由青年、政府和工業界組成的新型跨國聯盟來植樹,以應對這場環境災難。
權使命的開始
權講述了他阻止沙漠的工作是如何開始的:
“我阻止中國沙漠蔓延的努力始於一次非常獨特的個人經歷。 1998年,當我抵達北京擔任駐華大使時,迎接我的是沙塵暴。 帶來沙塵的大風非常猛烈,看到北京的天空異常黑暗,著實令人震驚。 第二天我接到女兒的電話,她說首爾的天空也被從中國吹來的沙塵暴覆蓋了。 我意識到她正在談論我剛剛目睹的同一場風暴。 那通電話讓我意識到了危機。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都面臨著一個超越國界的共同問題。 我清楚地看到,在北京看到的黃沙問題是我的問題,也是我家人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中國人需要解決的問題。”
權和未來森林的成員登上一輛巴士,乘坐一個小時,然後穿過一個小村莊,那裡的農民、牛和山羊都呆呆地看著這些奇怪的遊客。 然而,在田園風光的農田上步行 3 公里後,眼前的景像變成了可怕的幽靈:無邊無際的沙子一直延伸到地平線,沒有一絲生命的痕跡。
韓國年輕人和中國同行一起,很快就開始努力挖掘剩餘的表土,種植他們帶來的樹苗。 他們與韓國、中國、日本和其他地方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一起,投身於千禧年的挑戰:減緩沙漠的蔓延。
像庫布奇這樣的沙漠是年降雨量減少、土地利用不當以及內蒙古等發展中地區貧困農民不顧一切地試圖通過砍伐樹木和灌木叢來獲得一點現金的結果,這些樹木和灌木叢可以固定土壤並阻擋風。 ,用於柴火。
當被問及應對這些沙漠的挑戰時,權大使做了簡短的回應:“這些沙漠以及氣候變化本身對全人類來說是一個壓倒性的威脅,但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改變我們的預算優先事項。為了安全。”
權暗示我們關於安全的基本假設有可能發生根本性轉變。 現在我們正面臨氣候變化的先兆,無論是2012年夏天席捲美國的可怕野火,還是正在下沉的圖瓦盧國家所面臨的危險,我們知道需要採取嚴厲行動。 但我們每年花費超過一萬億美元購買導彈、坦克、槍支、無人機和超級計算機——這些武器在阻止沙漠蔓延方面的效果就像彈弓對付坦克一樣有效。 難道我們不需要在技術上實現飛躍,而是在安全術語上實現概念上的飛躍: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那些資金充足的軍隊的首要任務。
被沙漠淹沒還是被海洋淹沒?
氣候變化催生了兩個陰險的雙胞胎,它們正在貪婪地吞噬著美好地球的遺產:不斷擴大的沙漠和不斷上升的海洋。 當庫布奇沙漠向東延伸至北京時,它與亞洲、非洲和世界各地干旱地區其他正在崛起的沙漠攜手並進。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海洋正在上升,酸性越來越強,併吞沒了島嶼和大陸的海岸線。 在這兩種威脅之間,人類沒有多少餘地,也沒有閒暇時間去幻想兩大洲的戰爭。
地球變暖、水和土壤的濫用以及將土壤視為消耗品而不是維持生命的系統的不良農業政策,導致了農業用地的災難性減少。
聯合國於1994年制定了《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旨在聯合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應對沙漠的蔓延。 至少有十億人面臨著沙漠蔓延的直接威脅。 此外,由於過度耕作和降雨量減少對居住著另外 XNUMX 億人口的旱地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了影響,全球糧食生產和流離失所者的苦難受到的影響將會更大。
各大洲的沙漠現像如此嚴重,以至於聯合國將這十年定為“沙漠與防治荒漠化十年”,並宣布沙漠的蔓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環境挑戰”。
時任《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執行秘書 Luc Gnacadja 直言不諱地說 “表層 20 厘米的土壤是我們與滅絕之間的唯一障礙。
大衛·蒙哥馬利在他的著作《污垢:文明的侵蝕》中詳細描述了這種威脅的嚴重性。 蒙哥馬利強調,經常被視為“污垢”的土壤是一種戰略資源,比石油或水更有價值。 蒙哥馬利指出,自 38 年以來,全球 1945% 的農田已嚴重退化,目前農田侵蝕速度比其形成速度快 100 倍。 這一趨勢加上氣溫上升和降雨量減少,使美國“糧倉”西部地區的農業變得邊緣化,並受到暴雨侵蝕的加劇。 簡而言之,即使是美國乃至世界糧倉中心的部分地區,也正在變成沙漠。
蒙哥馬利認為,像內蒙古這樣當今遭受荒漠化的地區“就土壤而言,就像全球煤礦中的金絲雀”。 那些不斷擴大的沙漠應該是對我們即將發生的事情的警告。 “當然,在我的家鄉西雅圖,每年降雨量減少幾英寸,溫度升高一度,森林仍然常綠。 但如果你把一個乾旱的草地地區每年的降雨量減少幾英寸——它已經沒有那麼多降雨了。 植被減少、風蝕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壤枯竭就是我們所說的荒漠化。 但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正在看到世界各地的土壤退化,但我們只在這些脆弱地區清楚地看到了表現。”
與此同時,極地冰蓋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隨著海岸消失以及颶風桑迪等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發生,這將威脅沿海居民。 美國國家科學院於2012年8月發布了題為《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海岸海平面上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報告,預測到23年全球海平面將上升2030至2000厘米,相對於18年的水平,到48年將減少2050至50厘米,到140年將增加2100至2100厘米。報告對18年的估計大大高於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的59至XNUMX厘米,許多專家私下認為預計會出現更可怕的情況。 這場災難將發生在我們的子孫有生之年。
華盛頓特區政策研究所可持續能源和經濟網絡主任珍妮特·雷德曼 (Janet Redman) 在 40,000 英尺高的氣候峰會上觀察了氣候政策。 她提請人們注意颶風桑迪如何讓人們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全面影響:“桑迪颶風確實使氣候變化的威脅變得更加現實。 這樣的極端天氣,是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表示,這場颶風是‘氣候變化’的結果,他是一個非常主流的人。”
此外,當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請求聯邦資金重建海岸時,紐約市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走得更遠。 布隆伯格市長表示,我們需要使用聯邦資金開始重建紐約市本身。 “他明確表示海平面正在上升,我們現在需要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雷德曼回憶道。 “彭博社宣稱氣候變化已經到來。 他甚至建議我們需要恢復紐約市周圍的濕地來吸收此類風暴。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適應策略。 因此,極端天氣事件與公眾/媒體知名度較高的主流政客的有力論據相結合,有助於改變對話。 布隆伯格不是阿爾·戈爾; 他不是地球之友的代表。”
周圍的擔憂可能會凝結成對安全定義的新視角。 矽圖形公司 (Silicon Graphics Inc.) 前首席執行官羅伯特·畢肖普 (Robert Bishop) 創立了國際地球模擬中心,旨在讓政策制定者和業界了解當今的氣候變化。 Bishop 指出,桑迪颶風將花費約 60 億美元,卡特里娜颶風和威爾瑪颶風的總成本以及深水地平線漏油清理的最終成本將分別約為 100 億美元。
“我們談論的是每次造成 100 億美元損失的生態災難。” 他指出,“這類災難將開始改變五角大樓的觀點——因為它們顯然將整個國家置於危險之中。 此外,美國東海岸海平面上升可能會造成未來的重大損失。 很快將需要大量資金來保護沿海城市。 例如,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是東海岸唯一的核航母基地的所在地,而該城市已經遭受了嚴重的洪水問題。”
畢曉普接著解釋說,紐約市、波士頓和洛杉磯是美國的“文明核心中心”,它們都位於該國最脆弱的地區,而且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它們免受威脅,不是外國軍隊或導彈的影響,而是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為什麼氣候變化不被視為“威脅”
說我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環境危機是不正確的,但如果我們是一個面臨滅絕的物種,那麼我們就沒有做太多事情。
也許部分問題在於時間框架。 軍方傾向於快速思考安全問題:如何在幾個小時內保衛機場,或在幾分鐘內轟炸戰區內新獲得的目標? 整個情報收集和分析週期的加快加劇了這一趨勢。 我們需要能夠即時響應基於網絡的網絡攻擊或導彈發射。 雖然快速響應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光環,但快速響應的心理需求與真正的安全性關係不大。
如果主要的安全威脅要以數百年的時間來衡量怎麼辦? 軍事和安全界似乎沒有任何系統可以在如此長的時間內解決問題。 大衛·蒙哥馬利表示,這個問題是當今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例如,全球表土流失量每年約為 1%,這種變化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策雷達屏幕上是看不見的。 但這種趨勢將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對全人類造成災難,因為形成表土需要數百年的時間。 耕地的喪失,加上世界各地人口的迅速增長,無疑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之一。 然而安全界很少有人關注這個問題。
珍妮特·雷德曼建議,我們必須找到某種安全界可以接受的長期安全定義:“最終,我們需要開始從代際意義上考慮安全,即所謂的‘代際安全’。”世代安全。 也就是說,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將影響未來,將影響你的孩子、你的孫子以及我們以外的人。” 此外,雷德曼表示,氣候變化對許多人來說太可怕了。 “如果問題真的那麼嚴重,它可能會完全毀掉我們所重視的一切; 摧毀我們所知道的世界。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從交通到食物到事業、家庭; 一切都必須改變。”
賈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著作《崩潰:社會如何選擇失敗或生存》中指出,社會周期性地面臨著當前統治者的短期利益、他們舒適的習慣和子孫後代的長期利益之間的艱難選擇,而且他們很少做出選擇。表現出對“代際正義”的理解。 戴蒙德接著指出,所要求的變革越違背核心文化和意識形態假設,社會就越有可能陷入大規模否認。 例如,如果威脅的根源是我們盲目地認為物質消費體現了自由和自我實現,那麼我們可能會與消失的複活節島文明走在同一條軌道上。
也許當前對恐怖主義和無休止的軍事擴張的痴迷是一種心理否認,通過這種方式,我們通過追求不太複雜的問題來分散我們對氣候變化的注意力。 氣候變化的威脅是如此巨大和具有威脅性,以至於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在做什麼,問問自己是否每一次拿鐵咖啡或夏威夷假期都是問題的一部分。 將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山區的敵人身上要容易得多。
約翰·費弗(John Feffer)是《焦點外交政策》的主任,他嚴厲批評了他所說的“五角大樓的肥胖問題”,他最生動地總結了潛在的心理:
“我們被困在不斷蔓延的沙子和不斷上漲的海水之間,不知何故,我們根本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更不用說找到解決方案了。
“就好像我們正站在非洲大草原的中央。 一頭衝鋒的大像從一側向我們衝來。 另一邊,一頭獅子正要撲來。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專注於較小的威脅,例如基地組織。 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只爬到我們腳趾上並將下頜骨嵌入我們皮膚的螞蟻上。 當然很痛,但這不是主要問題。 我們太忙於低頭看腳趾,以至於看不到大象和獅子。”
另一個因素只是政策制定者和那些為我們提供信息的媒體創造者缺乏想像力。 許多人根本無法想像最壞的環境災難。 他們傾向於想像明天基本上會像今天一樣,進展永遠是線性的,對未來的任何預測的最終檢驗都是我們自己的個人經歷。 由於這些原因,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實際上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事情真的那麼嚴重,我們是否需要轉向軍事選擇?
稱讚美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軍隊,已經成為政客們的標準台詞。 但如果軍隊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沙漠蔓延和土壤消失的挑戰,我們的命運可能會像珀西·比希·雪萊的詩《奧茲曼迪亞斯》中被遺忘的皇帝一樣,他巨大的、毀壞的雕像上刻著這樣的銘文:
看看我的作品,你們全能者,絕望吧!
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圍繞腐爛
那巨大的殘骸,無邊無際,光禿禿的
孤寂平坦的沙地綿延很遠。
對抗不斷蔓延的沙漠和不斷上升的海洋將需要巨大的資源和我們所有的集體智慧。 應對措施不僅涉及重組我們整個政府和經濟,而且還涉及重建我們的文明。 但問題仍然存在:這種反應是否僅僅是對優先事項和激勵措施的重新調整,或者這種威脅是否真正相當於戰爭,即“全面戰爭”,僅在反應的性質和假定的“敵人”方面有所不同? 我們是否面臨著一場生死攸關的危機,需要大規模動員、控制和定量的經濟以及大規模的短期和長期戰略規劃? 簡而言之,這場危機是否需要戰爭經濟和對軍事體系的徹底反思?
採取軍事反應存在巨大風險,尤其是在暴力思想滲透到我們社會的時代。 當然,為環城公路強盜打開大門,在氣候變化的殿堂裡開展業務將是一場災難。 如果五角大樓利用氣候變化來證明在幾乎或根本不適用於實際威脅的項目上增加軍費是合理的,該怎麼辦? 我們知道,在傳統安全的許多領域,這種趨勢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然,存在著軍事文化和假設被錯誤地應用於氣候變化問題的危險,而這種威脅最終最好通過文化轉型來解決。 由於美國在抑制其使用軍事選擇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衝動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如果有的話)控制軍隊,而不是進一步助長軍事力量。
但就氣候變化而言,情況有所不同。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重塑軍隊是必要的一步,儘管存在風險,但這一過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整個安全系統的文化、使命和優先事項。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軍方進行辯論。
除非抓住真正的安全問題,從荒漠化和海平面上升到糧食短缺和人口老齡化,否則可能無法找到一個允許世界各國軍隊之間進行深入合作的集體安全架構。 畢竟,即使美軍撤軍或辭去世界警察的角色,整體安全局勢也可能變得更加危險。 除非我們能夠找到不需要共同潛在敵人的軍隊之間的合作空間,否則我們不太可能減少我們目前面臨的可怕風險。
詹姆斯·鮑德溫寫道:“並不是所有面臨的事情都可以改變,但如果不面對,什麼都無法改變。” 對於我們來說,希望軍隊自動變得不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們必須規劃出一條轉型之路,然後對軍隊施壓、推動,讓他們承擔新的角色。 因此,反對軍事介入的論點是有道理的,但事實是,軍方永遠不會同意大幅削減軍事預算,以支持通過其他機構應對氣候變化的支出。 相反,氣候變化的危險必須在軍隊中引起人們的注意。 此外,將可持續性作為軍隊的一項關鍵原則,可以通過將軍隊的能量引導到生態系統的修復中,從而極大地糾正困擾美國社會的軍國主義和暴力心態。
軍隊始終在準備打最後一場戰爭,這是一條不言而喻的真理。 無論是用咒語和長矛與歐洲殖民者作戰的非洲酋長,還是內戰時期的將軍們,他們熱衷於馬匹,蔑視骯髒的鐵路,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將軍們,他們將步兵師派遣到機槍掃射中,就像他們在與法普聯軍作戰一樣。戰爭中,軍方傾向於認為下一場衝突將只是上一場衝突的放大版。
如果軍方不再對伊朗或敘利亞構成軍事威脅,而是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其首要任務,那麼它將引進一批新的有才華的年輕男女,軍隊的角色將會發生轉變。 隨著美國開始重新分配其軍費開支,世界其他國家也將如此。 其結果可能是一個軍事化程度大大降低的體系,並可能成為全球合作的新要求。
但如果我們找不到辦法引導美軍朝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個概念就毫無用處。 事實上,我們在武器系統上花費的寶貴財富甚至不能滿足軍事需求,更不用說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任何應用。 約翰·費弗認為,官僚惰性和相互競爭的預算是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只能追求沒有明確用途的武器的主要原因:“軍隊的各個機構相互競爭,爭奪預算蛋糕的一塊,他們不希望看到他們的總預算下降。” 費弗暗示某些論點會被重複,直到它們看起來像福音:“我們必須維持我們的核三位一體; 我們必須擁有最低數量的噴氣式戰鬥機; 我們必須擁有一支適合全球強國的海軍。”
繼續建造更多相同設施的必要性也具有區域和政治因素。 與這些武器相關的工作分散在全國各地。 “每個國會選區都以某種方式與武器系統的製造有聯繫,”費弗說。 “這些武器的製造意味著就業機會,有時是唯一倖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 政治家不能忽視這些聲音。 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巴尼·弗蘭克最勇敢地呼籲軍事改革,但當該州生產的F-35戰鬥機的備用發動機需要投票時,他不得不投贊成票——儘管空軍聲明不需要。”
華盛頓特區的一些人已經開始對國家利益和安全制定更廣泛的定義。 最有前途的計劃之一是新美國基金會的智能戰略計劃。 在帕特里克·多爾蒂(Patrick Doherty)的指導下,一項“大戰略”正在形成,該戰略吸引了人們對社會和世界範圍內的四個關鍵問題的關注。 “大戰略”處理的問題是“經濟包容性”,未來3年全球20億人進入中產階級以及這一變化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生態系統耗竭”,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及其對我們的影響; “遏制蕭條”,當前經濟形勢的特點是需求低迷和嚴厲的緊縮措施; 以及“彈性赤字”,即我們的基礎設施和整體經濟體系的脆弱性。 “智慧戰略計劃”並不是要讓軍隊變得更加綠色,而是要重新調整包括軍隊在內的整個國家的總體優先事項。 多爾蒂認為,軍隊應該堅守原來的角色,不要擴展到超出其專業知識的領域。
當被問及五角大樓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總體反應時,他指出了四個不同的陣營。 首先,有些人仍然關注傳統的安全問題,並在計算中考慮到氣候變化。 還有一些人將氣候變化視為傳統安全規劃中必須考慮的另一個威脅,但更多的是外部因素而不是主要問題。 他們對水下海軍基地或兩極新海上通道的影響表示擔憂,但他們的基本戰略思維沒有改變。 還有一些人主張利用巨額國防預算來利用市場變化,著眼於影響軍事和民用能源使用。
最後,軍方人士得出的結論是,氣候變化需要一項涵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全新國家戰略,並與不同利益相關者就前進的道路進行廣泛對話。
關於如何重塑軍隊的一些想法,但要快!
我們必須制定一項軍隊計劃,將 60% 或更多的預算用於開發技術、基礎設施和實踐,以阻止沙漠蔓延、復興海洋,並將當今破壞性的工業體系轉變為新的可持續經濟。 一支以減少污染、監測環境、修復環境破壞和適應新挑戰為首要任務的軍隊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能否想像一支軍隊的主要使命不是殺戮和破壞,而是保存和保護?
我們呼籲軍隊做一些目前不適合做的事情。 但縱觀歷史,軍隊常常需要徹底改造自己以應對當前的威脅。 此外,氣候變化是我們文明從未遇到過的挑戰。 重組軍隊以應對環境挑戰只是我們將看到的眾多根本性變化之一。
對當前軍事安全體系各個部分進行系統性重新分配,將是從零星接觸轉向全面接觸的第一步。 海軍主要負責保護和恢復海洋; 空軍將負責大氣、監測排放並製定減少空氣污染的戰略; 而陸軍可以處理土地保護和水問題。 各分支機構將負責應對環境災害。 我們的情報部門將負責監測生物圈及其污染者,評估其狀況並提出長期的補救和適應建議。
這種方向的徹底轉變帶來了幾個主要優勢。 最重要的是,它將恢復武裝部隊的目標和榮譽。 武裝部隊曾經是美國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的徵召地,產生了喬治·馬歇爾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這樣的領導人,而不是像大衛·彼得雷烏斯這樣的政治內鬥者和自以為是的人。 如果軍隊的需要發生轉變,它將重新獲得在美國社會中的社會地位,其軍官將能夠再次在促進國家政策方面發揮核心作用,而不會袖手旁觀,因為武器系統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追求的。遊說者及其企業贊助商。
美國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決定:我們可以被動地走上軍國主義和帝國衰落的必然道路,或者從根本上將目前的軍工聯合體轉變為真正的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模式。 後一條道路為我們提供了糾正美國失誤的機會,並朝著更有可能從長遠來看適應和生存的方向出發。
讓我們從太平洋樞紐開始
約翰·費弗建議,這種轉變可以從東亞開始,並採取擴大奧巴馬政府大肆宣揚的“太平洋支點”的形式。 費弗表示:“太平洋樞軸戰略可以成為更大聯盟的基礎,該聯盟將環境作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之間安全合作的中心主題,從而減少對抗和衝突的風險。”重新武裝。” 如果我們關注真正的威脅,例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不是可持續增長)如何導致了沙漠的蔓延、淡水供應的減少以及鼓勵盲目消費的消費文化,我們就可以降低以下風險:該地區的軍備集結。 隨著東亞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不斷增強,並以世界其他地區為基準,安全概念的區域轉變以及軍事預算的相關變化可能會對全球產生巨大影響。
那些認為新“冷戰”正在席捲東亞的人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在經濟快速增長、經濟一體化和民族主義方面,今天的東亞與意識形態冷戰時期的東亞之間並不存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處。而是今天的東亞與 1914 年的歐洲之間。在那個悲慘的時刻,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奧匈帝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一體化之中,儘管有持久和平的談論和希望,但未能解決長期存在的歷史問題。問題並陷入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假設我們面臨另一場“冷戰”,就忽視了軍事建設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內部經濟因素驅動的,與意識形態無關。
100年,中國的軍費開支首次達到2012億美元,其兩位數的增長促使鄰國也增加了軍事預算。 韓國正在增加軍費開支,預計5年增長2012%。儘管日本將軍費開支保持在GDP的1%,但新當選的首相安倍晉三呼籲大幅增加日本海外開支對中國的敵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五角大樓鼓勵其盟友增加軍費開支併購買美國武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五角大樓預算的潛在削減常常被視為其他國家增加軍費開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機會。
結論
權大使的未來森林在將韓國和中國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植樹並建造遏制庫布奇沙漠的“綠色長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與古代的長城不同,這堵牆的目的不是為了抵禦人類敵人,而是為了創造一排樹木作為環境防禦。 或許東亞和美國政府可以藉鑑這些孩子的榜樣,將環境和適應作為首要議題,為長期癱瘓的六方會談注入活力。
如果擴大對話的範圍,軍事和民間組織之間在環境方面的合作潛力是巨大的。 如果我們能夠將地區競爭對手聯合起來,實現共同的軍事目標,而無需與“敵國”緊密合作,我們也許能夠避免當今最大的危險之一。 緩和競爭和軍事集結局勢的效果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好處,與氣候響應任務所做出的貢獻截然不同。
六方會談可以演變成一個“綠色支點論壇”,評估環境威脅,確定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優先事項,並分配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