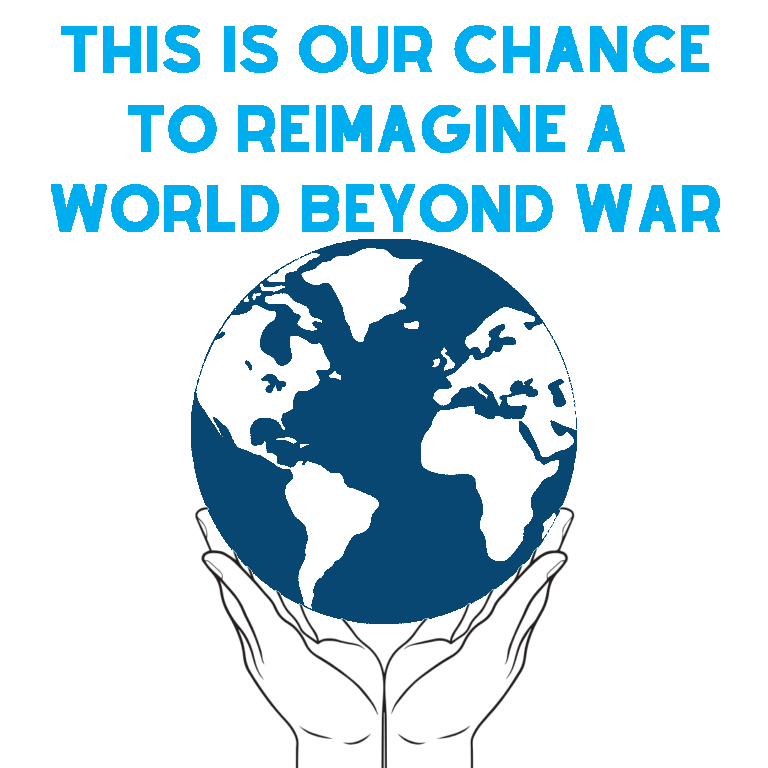By 布賴恩·威爾森
1914 年100,000 月,令人驚奇的和平爆發了,儘管時間很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駐紮在500 英里西線沿線的24 萬軍隊中,有多達36 萬人(即24%)相互自發地停止了戰鬥,至少在26 月 11 日至 1915 日,115 至 30 小時。 局部停戰事件至少早在 40 月 XNUMX 日就曾發生過,並且零星地持續到元旦和 XNUMX 年 XNUMX 月初。英國、德國、法國和比利時士兵中至少有 XNUMX 支戰鬥部隊參與其中。 儘管將軍下令嚴格禁止與敵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友好交往,但前線的許多地點都可以看到樹上點著蠟燭,士兵們從相距XNUMX到XNUMX碼的戰壕中走出來,與敵人握手、分享煙、食物和酒,並與敵人唱歌。另一個。 各方軍隊紛紛趁機掩埋戰場上各自的陣亡將士,甚至有報導說存在聯合合葬的情況。 在某些情況下,軍官們也加入了廣泛的兄弟情誼之中。 甚至有時還提到德國人和英國人之間進行的一場足球比賽。 (參見來源)。
儘管這是人類精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但這並不是戰爭史上的獨特事件。 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確立的傳統的複興。 在幾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的其他長期軍事戰鬥中,也發生過非正式休戰和小規模局部停戰以及敵人之間的友誼事件。[1] 這也包括越南戰爭。[2]
軍事科學教授、退役陸軍中校戴夫·格羅斯曼認為,人類對殺戮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與生俱來的抵抗力,需要特殊訓練才能克服。[3] 1969 年初,在美國空軍遊騎兵訓練期間,我無法將刺刀刺入假人。我想,如果我是一名陸軍士兵,而不是一名空軍軍官,並且年輕幾歲,那麼在飛機上殺人會更容易嗎?命令? 當我拒絕使用刺刀時,我的指揮官顯然非常不高興,因為軍隊很清楚,只有通過強製手段才能使人殺人。 軍隊運作所需的暴政是殘酷的。 它知道它不能允許就其使命進行對話,並且必須迅速修補盲目服從系統中的任何裂縫。 我立即被列入“軍官控制名單”,並在閉門的情況下面臨皇室的責罵,我被威脅要上軍事法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羞辱,並被指控為膽小鬼和叛徒。 我被告知,我無意識地拒絕參加刺刀演習,造成了士氣問題,有可能干擾我們的任務。
1961 年,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 因協調大屠殺而在耶路撒冷受審僅三個月後,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開始了一系列實驗,以更好地理解服從權威的本質。 結果令人震驚。 米爾格拉姆仔細篩選了他的研究對象,使其能夠代表典型的美國人。 在簡要介紹了遵守命令的重要性之後,每當附近的學習者(演員)在單詞匹配任務中犯錯時,參與者就會被指示按下一個槓桿,造成他們認為的一系列電擊,並以十五伏的增量逐漸升級。 。 當學習者開始痛苦地尖叫時,實驗者(權威人物)平靜地堅持實驗必須繼續。 令人吃驚的是,米爾格拉姆的參與者中有 65% 的人使用了盡可能高的電流——這種致命的震動可能會導致真正受到電擊的人死亡。 多年來在美國其他大學以及歐洲、非洲和亞洲的至少九個其他國家進行的其他實驗都顯示出類似的高服從率。 2008 年的一項研究旨在復制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同時避免其中幾個最具爭議的方面,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4]
米爾格拉姆宣布了這項研究最基本的教訓:
普通人,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沒有任何特別的敵意,就可以成為可怕的破壞性過程的推動者。 。 。 服從主體最常見的思想調整是他(她)認為自己對自己的行為不負有責任。 。 。 他(她)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以道德負責任的方式行事的人,而是外部權威的代理人,“儘自己的職責”,這在紐倫堡被告的辯護陳述中一次又一次地聽到。 。 。 。 在復雜的社會中,當一個人只是邪惡行為鏈條中的一個中間環節,但距離最終後果還很遠時,人們在心理上很容易忽視責任。 。 。 。 因此,整個人類行為是支離破碎的。 沒有一個男人(女人)決定實施邪惡行為並承擔其後果。[5]
米爾格拉姆提醒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歷史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就會發現,既定權威的“民主”同樣是殘暴的,它的繁榮依賴於一群順從的貪得無厭的消費者,依賴於他人的恐嚇,並列舉了對原始土著居民的破壞,對奴隸制的依賴。數百萬人、日裔美國人的拘留以及對越南平民使用凝固汽油彈。[6]
正如米爾格拉姆報導的那樣,“只要能夠控制住一個人的叛逃,就不會造成什麼後果。 他將被隊列中的下一個人接替。 對軍事運作的唯一危險在於,一個單獨的叛逃者可能會刺激其他人。”[7]
1961年,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一位猶太人,目睹了對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 她驚訝地發現他“既不變態也不虐待狂”。 相反,艾希曼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可怕的正常人”。[8] 阿倫特將普通人由於社會壓力或在某種社會環境下犯下非凡邪惡的能力描述為“邪惡的平庸”。 從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我們知道“邪惡的平庸性”並不是納粹獨有的。
生態心理學家和文化歷史學家認為,植根於相互尊重、同理心和合作的人類原型對於我們物種在進化分支上走得這麼遠非常重要。 然而,5,500 年前,即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相對較小的新石器時代村莊開始轉變為更大的城市“文明”。 隨著“文明”的出現,一種新的組織理念出現了——文化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稱之為“巨型機器”,它完全由人類“部分”組成,被迫協同工作,以執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任務。 文明見證了由權威人物(國王)與抄寫員和信使組成的權力複合體指揮的官僚機構的建立,它們組織勞動機器(大量工人)建造金字塔、灌溉系統和巨大的糧食儲存系統以及其他結構,所有這些由軍隊強制執行。 其特點是權力集中、階級分化、強迫勞動和奴隸制的終生劃分、財富和特權的任意不平等、軍事力量和戰爭。[9]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被教導認為文明對人類狀況如此有益,但事實證明,它對我們物種造成了嚴重的創傷,更不用說對其他物種和地球生態系統了。 作為我們這個物種的現代成員(不包括幸運的土著社會,他們以某種方式逃脫了同化),我們三百代以來一直被困在一個需要大規模服從大型垂直權力複合體的模式中。
芒福德明確表示了他的偏見,即小型橫向群體的自主權是一種人類原型,但現在由於對技術和官僚機構的服從而受到壓抑。 人類城市文明的創造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系統性暴力和戰爭模式,[10] 安德魯·施穆克勒(Andrew Schmookler)稱之為文明的“原罪”,[11] 和芒福德,“集體偏執和部落的偉大妄想。”[12]
“文明”需要大量的民間力量 服從 使垂直權力結構佔上風。 無論這種等級制垂直權力是如何實現的,無論是通過君主繼承、獨裁者還是民主選舉,它總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暴政來發揮作用。 人們曾經在前文明部落群體中享有的自治自由現在服從於對權威結構及其控制意識形態的信仰,這些結構被描述為壓迫性的“統治等級制度”,私有財產和男性對女性的征服盛行,必要時還可以使用武力。[13]
垂直權威結構的出現,即國王和貴族的統治,使人們擺脫了小部落群體的歷史生活模式。 除了強制分層之外,人們與地球的親密聯繫的分離也給心靈帶來了深深的不安全感、恐懼和創傷。 生態學家認為,這種分裂導致了生態 un意識。[14]
因此,人類迫切需要重新發現和培育不服從政治權威體系的例子,自大約 14,600 年前文明出現以來,這些體系已經製造了 5,500 場戰爭。 在過去的3,500年裡,為了結束戰爭,已經簽署了近8,500個條約,但都無濟於事,因為權力的垂直結構仍然完好無損,這要求他們在擴大領土、權力或資源基礎的努力中服從。 當我們等待人類個人和集體恢復正常思維時,該物種的未來以及大多數其他物種的生命都受到威脅。
一百年前的 1914 年聖誕節休戰是一個非凡的例子,說明只有士兵同意戰鬥,戰爭才能繼續下去。 它需要被尊重和慶祝,即使這只是一瞬間的事。 它代表了人類不服從瘋狂政策的可能性。 正如德國詩人和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所宣稱的那樣, 將軍,你的坦克是一輛強大的車輛。 它摧毀了森林,壓碎了一百個人。 但它有一個缺陷:它需要一個驅動程序。[15] 如果平民拒絕集體駕駛戰爭坦克,那麼領導人將只能自己打仗。 它們會很簡短。
尾注
[1] http://news.bbc.co.uk/2/hi/special_report/1998/10/98/world_war_i/197627.stm,信息取自 Malcolm Brown 和 Shirley Seaton, 聖誕休戰:西線,1914 年 (紐約:Hippocrene Books,1984 年。
[2] 理查德·博伊爾, 龍之花:美軍在越南的崩潰 (舊金山:Ramparts Press,1973),235-236; 理查德·莫澤, 新冬兵,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996 年),132; 湯姆·威爾斯, 內戰爭 (紐約:Henry Holt and Co.,1994),525-26。
[3] 戴夫格羅斯曼, 論殺戮:學習戰爭與社會的心理成本 (波士頓:Little,Brown,1995)。
[4] 麗莎·克里格 (Lisa M. Krieger),“令人震驚的啟示:聖克拉拉大學教授反映了著名的酷刑研究” 聖何塞水星報, 十二月20,2008。
[5]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服從的危險》 哈珀的, 1973 年 62 月,66–75、77–XNUMX;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服從權威:實驗觀點 (1974 年;紐約:常年經典,2004 年),6-8,11。
[6] 米爾格拉姆,179。
[7] 米爾格拉姆,182。
[8]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 (1963 年;紐約:企鵝圖書,1994 年),276]。
[9] 劉易斯·芒福德, 機器的神話:技術與人類發展 (紐約:哈考特、布雷斯和世界公司,1967 年),186。
[10]阿什利·蒙塔古, 人類侵略的本質 (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 年),43-53、59-60; 阿什利·蒙塔古編輯, 學習非攻擊性:無文化社會的經驗 (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8); 讓·吉萊恩和讓·扎米特, 戰爭的起源:史前時期的暴力, 跨。 梅蘭妮·赫西(2001 年;馬薩諸塞州馬爾登:布萊克韋爾出版社,2005 年)。
[11] 安德魯·B·施莫克勒, 走出軟弱:治愈驅使我們走向戰爭的創傷 (紐約:Bantam Books,1988),303。
[12] 芒福德,204。
[13] 艾蒂安·德拉博埃蒂, 服從的政治:自願奴役的話語, 跨。 Harry Kurz(約 1553 年;蒙特利爾:Black Rose Books,1997),46, 58–60; 瑞安·艾斯勒, 聖杯與刀鋒 (紐約:Harper & Row,1987),45-58,104-6。
[14] Theodore Roszak、Mary E. Gomes 和 Allen D. Kanner 編輯, 生態心理學:恢復地球治愈心靈 (舊金山:塞拉俱樂部圖書,1995 年)。 生態心理學的結論是,如果不治愈地球,就不可能有個人治愈,而重新發現我們與地球的神聖關係,即我們親密的泥土性,對於個人和全球治愈以及相互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15] “將軍,你的坦克是一輛強大的車輛”,發表於 摘自德國戰爭入門書,一部分的 斯文堡詩歌 (1939); 譯者:Lee Baxandall 詩歌,1913-1956289。
消息來源 1914 年聖誕節休戰
http://news.bbc.co.uk/2/hi/special_report/1998/10/98/world_war_i/197627.stm.
布朗、大衛. “銘記人類善良的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令人費解、令人心酸的聖誕休戰” “華盛頓郵報”, 十二月25,2004。
布朗、馬爾科姆和雪莉·西頓。 聖誕休戰:西線,1914 年。 紐約:希波克林,1984。
克利弗、艾倫和萊斯利·帕克。 “聖誕休戰:總體概述”,christmastruce.co.uk/article.html,30 年 2014 月 XNUMX 日訪問。
吉爾伯特、馬丁. 第一次世界大戰:完整的歷史。 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94 年,117-19。
霍克希爾德、亞當. 結束所有戰爭:忠誠與叛逆的故事,1914-1918。 紐約:水手圖書,2012 年,130-32。
文奇格拉、托馬斯. “聖誕節休戰,1914”, 紐約時報,十二月25,2005。
溫特勞布、斯坦利. 《平安夜:第一次世界大戰聖誕休戰的故事》。 紐約:自由新聞社,2001 年。
----
S. Brian Willson,brianwillson.com,2 年 2014 月 72 日,退伍軍人和平分會第 XNUMX 章成員,俄勒岡州波特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