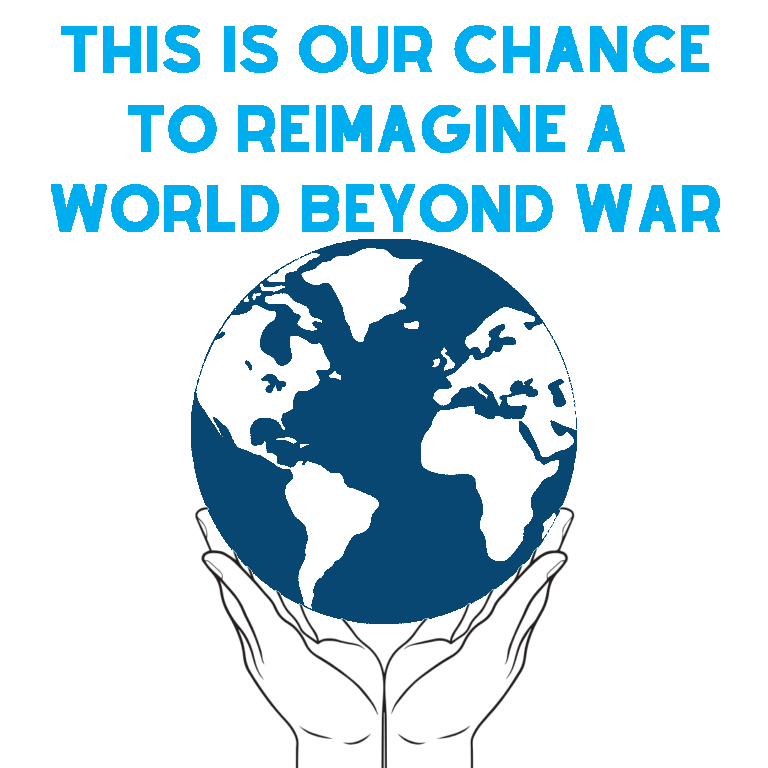戰爭或殺戮沒有什麼光榮的。 戰爭給人類造成的損失遠遠超出了戰場——它對幾代人的配偶、孩子、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表兄弟姐妹、阿姨和叔叔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人們還發現,歷史上大多數士兵都不願意殺死其他人,這樣做顯然違背了他們的本性。 作為使用暴力解決衝突的許可,戰爭中殺戮的後果是可怕的……而國家批准的暴力的後果通常對所謂的贏家和輸家來說都是毀滅性的。 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喬治·布什曾說過,我們面臨著韓國、伊朗和伊拉克“邪惡軸心”的危險。 不幸的是,奧巴馬政府隨後增加了目標國家的數量。 而馬丁·路德·金說,世界上最棘手的罪惡是貧困、種族主義和戰爭。 金的三重邪惡每天都在美國的國內和國際政策中上演。 或許,如果布什和當時的奧巴馬真的對結束恐怖主義感興趣,他們就會更仔細地研究金的更為深刻的分析。
縱觀歷史,關於如何最好地解決衝突的爭論一直存在。 選擇通常是暴力和不同的非暴力方法。 國家內部的“個人”如何解決衝突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如何解決之間的態度似乎也存在明顯差異。 貧困、種族主義和戰爭正是在這些衝突及其解決方案中相互作用。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通過非暴力方法(即討論、口頭協議)解決個人衝突。 金博士表示,非暴力社會變革或非暴力解決衝突的目的不是尋求報復,而是改變所謂敵人的心。 “我們永遠不能通過以恨應對來擺脫仇恨; 我們通過消除敵意來消滅敵人,”他說。 仇恨的本質就是毀滅和撕裂。”
大多數國家還制定了禁止個人使用暴力的法律。 例如,在美國公民社會,一個人不應該故意殺害另一個人。 如果是這樣,他們很容易受到國家起訴,在陪審團審判後,國家可能會因犯下此類罪行而殺死該人。 然而,在美國,懲罰通常是針對那些沒有資源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唯一仍然使用死刑的西方國家,死刑總是被強加於赤貧人口,尤其是有色人種——這些人通常沒有足夠的資金自衛。 死刑是國家批准暴力(或恐怖)作為解決衝突的一種方式的深刻例子。 用金博士的話說,美國的國內政策是種族主義的,本質上是針對窮人的戰爭,而且死刑表明了人們不願意寬恕。
幾年前,我想更多地了解戰爭,並天真地調查了我父親在二戰期間在德國參戰的一些朋友。 他們不肯和我說話。 他們不會分享任何東西。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他們拒絕的含義。 我後來了解到,戰爭是暴力、痛苦和痛苦的代名詞,因此大多數人不願意分享這些經歷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他的書中 每個人都應該了解的戰爭知識”,記者克里斯·赫奇斯寫道,“我們崇尚戰爭。 我們把它變成娛樂。 在這一切中,我們忘記了戰爭是什麼,忘記了戰爭對受苦受難的人們造成的影響。 我們要求軍人及其家人做出犧牲,為他們的餘生增添色彩。 我發現,最討厭戰爭的人都是了解戰爭的退伍軍人。”
在解決“國家之間”的衝突時,至少在理性的人們之間,出於多種原因,戰爭總是被認為是最後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巨大的破壞力。 “正義戰爭”的概念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嘗試了一切其他辦法來解決衝突。 儘管如此,再次引用金博士的話,他明智地問道,為什麼“在自己國家謀殺公民是犯罪行為,但在戰爭中謀殺另一個國家公民是英雄美德的行為?”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價值觀是扭曲的。
美國有著使用過度暴力來解決國際衝突的悲慘歷史,通常是為了控制和獲取石油等自然資源。 美國很少對其發動戰爭的真正原因保持透明。 虛偽是赤裸裸的,同時我們的年輕人卻被教導去殺人。
美國戰爭的目標與種族主義、貧困和戰爭三重罪惡有相似之處,與我們國內舞台上受到懲罰的人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 這些人總是窮人和有色人種,而不是主要是富有的白人腐敗銀行家、企業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等。美國司法和法院系統嚴重缺乏問責制,總體而言,階級問題和不平等極其重要。不平等現像變得更加極端。 儘管如此,弗格森事件和美國各地無數其他導致黑人生命悲劇性損失的事件當然會作為美國典型行為的熟悉例子浮現在腦海中。 就像在我們的國內舞台一樣,美國的入侵主要是針對極其貧窮、裝備落後和有色人種居住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美國至少可以保證獲得短期勝利。
暴力對我們社會產生“殘酷”影響。 無論如何,這對我們都沒有好處。 幾年前,英國人類學家科林·特恩布爾研究了死刑對美國的影響。 他採訪了死囚牢房的看守、拉動電刑開關的人、死囚牢房的囚犯以及所有這些人的家人。 對於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家屠殺的人來說,普遍存在的負面心理影響和健康問題是深遠的。 沒有人逃脫了恐怖。
社會學家也開始關注“戰爭”對社會的影響。 它還對我們產生“殘酷”的影響。 眾所周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我們個人行為的是我們周圍的家庭和同齡人。 但社會學家沒有關注國家政策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一些社會學家發現,戰後,衝突中的輸家和贏家的國家中個人使用暴力的情況都有所增加。 社會學家研究了暴力退伍軍人模型、經濟破壞模型等來解釋這一現象。 唯一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國家接受使用暴力來解決衝突。 當從行政部門到立法機關再到法院的所有政府部門都接受暴力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時,它似乎會滲透到個人——這基本上是為我們的國家使用或認為暴力是可接受的做法開了綠燈。日常生活。
也許反對讓我們的年輕男女參戰的最令人信服的論據之一是我們大多數人根本不想殺人。 儘管我們被教導戰鬥可能是多麼光榮,但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遵守殺戮的要求。 在他引人入勝的書中 論殺戮:學習戰爭與社會的心理成本 (1995),心理學家戴夫·格羅斯曼中校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講述“歷史上的不開火者”。 研究發現,縱觀歷史,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只有15%到20%的士兵願意殺人。 這種低百分比是普遍存在的,適用於歷史上每個國家的士兵。 有趣的是,即使遠離敵人也不一定會鼓勵殺戮。 格羅斯曼提供了一個令人著迷的發現:“即使有這一優勢,二戰期間被擊落的敵方飛行員總數的 1% 也只占到了 40% 的美國戰鬥機飛行員; 大多數人沒有擊落任何人,甚至沒有試圖擊落任何人。”
美國顯然不欣賞殺手比例如此之低,因此開始改變軍隊訓練方式。 美國人開始在訓練中結合使用IP·巴甫洛夫和BF·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通過重複使我們的士兵變得麻木。 一名海軍陸戰隊員告訴我,在基礎訓練中,你不僅要不斷地“練習”殺戮,而且幾乎每一個命令都要求你說“殺戮”這個詞。 “基本上,士兵已經將這個過程演練了很多次,”格羅斯曼說,“當他在戰鬥中殺人時,他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否認自己實際上正在殺死另一個人。” 到朝鮮戰爭時,55% 的美國士兵能夠殺人,而到了越南戰爭,這一比例達到了驚人的 95%。 格羅斯曼還指出,越南現在被稱為第一場藥物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軍給我們的士兵餵食大量藥物,以麻痺他們的感官,同時他們進行暴力行為,他們很可能在伊拉克做同樣的事情。
在談到戰鬥中殺手比例低的問題時,格羅斯曼說:“當我從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和士兵的角度研究這個問題並研究戰鬥中的殺戮過程時,我開始意識到,對戰鬥中殺戮的共同理解中缺少一個主要因素,這個因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等等。 這個缺失的因素是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即大多數人內心都強烈抵制殺害自己的同胞。 這種抵抗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在很多情況下,戰場上的士兵在克服它之前就會死去。”
我們不想殺人這一事實是對我們人性的謝意肯定。 我們真的想改變我們年輕男女的行為方式,使其成為專業、熟練的殺手嗎? 我們真的想以這種方式改變年輕人的行為嗎? 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對自己和他人的人性不敏感嗎? 難道我們不應該解決世界上真正的邪惡嗎?真正的邪惡軸心是種族主義、貧困和戰爭以及所有這些,再加上以犧牲我們所有人為代價來控制世界資源的貪婪? 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稅款被用來殺害世界上的窮人,摧毀他們的國家,並在這個過程中讓我們所有人變得更加暴力嗎? 我們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Heather Gray 在 WRFG-Atlanta 89.3 FM 上製作“Just Peace”節目,報導當地、地區、國家和國際新聞。 1985-86 年,她在亞特蘭大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指導非暴力項目。 她住在亞特蘭大,聯繫方式: justpeacewrfg@a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