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莎拉·弗拉托·曼薩拉 (Sarah Flatto Mansarah),8 年 2019 月 XNUMX 日
起 發動非暴力
就在一年前,以色列邊防警察暴力逮捕一名男子的照片和視頻 年輕的巴勒斯坦婦女 病毒式傳播。 當他們扯下她的頭巾並將她摔倒在地時,她似乎在尖叫。
它捕捉到了 4 年 2018 月 XNUMX 日的危機時刻,當時以色列軍隊帶著推土機抵達汗阿馬爾,準備用槍威脅驅逐並摧毀這個巴勒斯坦小村莊。 這是殘酷劇場中不可磨滅的一幕,它定義了 被圍困的村莊。 數百名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與軍隊和警察會面,他們動員起來將自己的身體置於危險之中。 他們與神職人員、記者、外交官、教育家和政治家一起,吃飯、睡覺、制定戰略並持續對即將到來的拆除進行非暴力抵抗。
在警方逮捕照片中的年輕女子和其他活動人士後,居民立即向最高法院提交請願書,要求停止拆遷。 已發布緊急禁令暫時停止該活動。 最高法院要求雙方達成一項“協議”來解決這一問題。 然後,法院宣布汗阿馬爾居民必須同意強行搬遷到東耶路撒冷垃圾場附近的一個地點。 他們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並重申了留在家中的權利。 最終,5年2018月XNUMX日,法官駁回了之前的請願,並裁定拆遷可以繼續進行。

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的社區習慣於被迫流離失所,特別是在 C區,完全處於以色列軍事和行政控制之下。 頻繁拆除 是以色列政府宣布的計劃的決定性策略 吞併全部巴勒斯坦領土。 汗阿馬爾橫跨以色列稱為“E1”地區的獨特關鍵位置,位於兩個根據國際法非法的以色列大型定居點之間。 如果汗阿馬爾被摧毀,政府將成功地在約旦河西岸設計毗連的以色列領土,並切斷巴勒斯坦社會與耶路撒冷的聯繫。
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政府拆除該村莊的計劃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譴責。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 發表聲明 “在沒有軍事必要的情況下大規模破壞財產以及在被佔領土上轉移人口構成戰爭罪。” 這 歐盟警告 拆除的後果將“非常嚴重”。 全天候的大規模非暴力抗議活動一直對汗·阿馬爾保持警惕,直到 2018 年 XNUMX 月下旬,以色列政府宣布將“撤離” 延遲,歸咎於選舉年的不確定性。 當抗議活動最終平息時,數百名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國際人士保護了該村莊四個月。
拆除工作獲得批准一年多後,汗·阿馬爾終於鬆了一口氣。 其人民仍留在家中。 他們意志堅定,決心留在那裡,直到被物理移除。 照片中的年輕女子莎拉已成為女性領導的抵抗運動的另一個標誌。
什麼是對的?
2019 年XNUMX 月,我坐在Khan al-Amar 與爆紅照片中的女人Sarah Abu Dahouk 和她的母親Um Ismael(出於隱私考慮,無法使用她的全名)一起喝鼠尾草茶,吃椒鹽捲餅。 在村子入口處,男人們斜靠在塑料椅子上吸水煙,孩子們則在玩球。 在這個被大片光禿禿的沙漠支撐的偏僻社區裡,有一種受歡迎的感覺,但又有些猶豫的平靜。 我們談論了去年夏天的生存危機,委婉地將其稱為 穆什基萊,或阿拉伯語問題。

距離以色列定居者經常光顧的一條繁忙高速公路僅數米之遙,如果我沒有和莎羅娜·韋斯(Sharona Weiss)在一起,我就不可能找到汗·阿馬爾。莎羅娜·韋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美國人權活動家,去年夏天在那里呆了幾週。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急轉彎,越野了幾米,來到了村口。 即使是最右翼的人也感覺很荒謬 卡漢主義者 至上主義者可能會認為這個社區(由數十個住在帳篷或木製和錫製棚屋中的家庭組成)對以色列國構成威脅。
莎拉只有 19 歲,比我從她沉著自信的舉止中猜想的要年輕得多。 我們咯咯地笑了,因為我們都是薩拉家族的人,嫁給了穆罕默德家族,或者說嫁給了穆罕默德家族。 我們都想要一群孩子,男孩和女孩。 當莎羅娜六歲的兒子在棚屋裡迷失時,伊斯梅爾正在和我三個月大的孩子玩耍。 “我們只想平靜地生活在這裡,過上正常的生活,”烏姆·伊斯梅爾熱情地反复說道。 莎拉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現在很高興。 我們只想一個人呆著。”
他們的背後沒有任何陰險的政治算計 蘇木德,或堅定。 他們兩次因以色列國而流離失所,他們不想再次成為難民。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巴勒斯坦社區的常見說法,但願世界願意傾聽。
去年,當莎拉試圖保護叔叔免遭逮捕時,她的頭巾被全副武裝的男警察扯掉了。 當她掙扎著逃跑時,他們又把她按倒在地抓捕。 這種特別殘酷和性別暴力引起了全世界對這個村莊的關注。 該事件在多個層面上都嚴重違反了規定。 隨著這張照片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她與當局、活動人士和村民的個人接觸現在被擴大到全世界。 即使那些自稱支持阿馬爾汗鬥爭的人也毫不猶豫地傳播這張照片。 在一個 以前的帳戶 在阿米拉·哈斯 (Amira Hass) 的撰寫中,家庭朋友解釋了這一事件所引發的深深的震驚和羞辱:“將手放在頭巾上就是損害女性的身份。”
但她的家人並不希望她成為“英雄”。 村里的領導認為她的被捕是可恥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非常關心家人的安全和隱私。 他們對一名年輕女子被拘留和監禁的想法感到心煩意亂。 一群來自汗阿馬爾的男子厚顏無恥地到法庭去代替莎拉被捕。 不出所料,他們的提議被拒絕了,她仍被拘留。

莎拉與她被關押在同一所軍事監獄 阿赫德·塔米米, 一名因掌摑士兵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青少年,以及她因拍攝這一事件而入獄的母親納里曼。 以色列公民巴勒斯坦作家達琳·塔圖爾 (Dareen Tatour) 也因罪名與他們一起入獄。 在 Facebook 上發表一首詩 被視為“煽動”。 他們都提供了急需的情感支持。 納里曼是她的保護者,當牢房太擁擠時,他會慷慨地為她提供床位。 在軍事聽證會上,當局宣布莎拉是汗阿馬爾地區唯一被指控犯有“安全罪”的人,目前她仍被拘留。 對她的可疑指控是她試圖襲擊一名士兵。
你鄰居的血
薩拉的母親烏姆·伊斯梅爾 (Um Ismael) 被認為是社區的支柱。 在整個拆遷危機期間,她讓村里的婦女了解情況。 部分原因是她的家位於山頂,位置便利,這意味著她的家人經常首先面臨警察和軍隊的入侵。 她還是為兒童提供物資和捐款的活動人士的聯絡人。 眾所周知,即使推土機開進來摧毀她的家,她也會開玩笑並保持高昂的情緒。
莎羅娜、莎拉和烏姆·伊斯梅爾帶我參觀了村莊,包括一所小學校,上面覆蓋著色彩繽紛的藝術品,該學校即將被拆除。 它通過成為一個居住抗議場所並接待活動人士數月而得以挽救。 更多的孩子出現了,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齊聲“哈嘍,你好嗎?” 他們和我的小女兒一起玩耍,第一次向她展示如何在捐贈的操場上滑滑梯。
當我們參觀學校和一個大型永久性帳篷時,莎羅娜總結了去年夏天的非暴力抵抗活動,以及為什麼它如此有效。 “從七月到十月,學校裡每天晚上都有輪班監視和靜坐抗議帳篷,”她解釋道。 “貝都因婦女沒有留在主要的抗議帳篷裡,但烏姆·伊斯梅爾告訴女性活動人士,歡迎她們睡在她家裡。”

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國際活動人士每天晚上都聚集在學校進行戰略討論,並一起享用由當地婦女瑪麗亞姆準備的豐盛大餐。 原本因意識形態差異而無法合作的政黨和領導人在阿馬爾汗的共同事業周圍團結起來。 瑪麗雅姆還確保每個人都始終有一個可以睡覺的墊子,並且無論情況如何,他們都感到舒適。
婦女們堅定地站在前線,對抗警察的侵略和胡椒噴霧,而有關婦女可能採取的行動的想法也隨之蔓延開來。 他們經常挽著手坐在一起。 在戰術上存在一些分歧。 一些婦女,包括貝都因婦女,想在驅逐地點周圍圍成一圈,唱歌,堅強地站著,並一前一後遮住臉,因為她們不想出現在照片中。 但男人們經常堅持要求婦女們去路另一邊沒有受到威脅的社區,這樣她們就可以免受暴力侵害。許多個夜晚,大約有 100 名活動人士、記者和外交官到達現場。與居民的關係,或多或少取決於拆除或週五祈禱的預期。 這種強大的團結讓人想起利未記 19:16 的誡命:不要袖手旁觀,讓你的鄰舍流血。.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風險最初讓當地人感到不安,但一旦以色列人被捕並表明他們願意為村莊承擔風險,這就不再是一個問題。 這些共同抵抗的行為受到了生存受到威脅的社區的熱情款待。

在軍隊和定居者的暴力事件屢見不鮮的 C 區,婦女往往可以在“解除逮捕”巴勒斯坦人的過程中發揮獨特而強大的作用。 當婦女們跳進來並開始對著她們大喊大叫時,軍隊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種直接行動通常可以通過中斷拘留來防止活動人士被捕並被帶離現場。
汗阿馬爾的“漂亮娃娃”
在抗議期間,國際和以色列婦女注意到,由於當地的隱私和性別隔離規範,當地婦女沒有來到公共抗議帳篷。 當地非營利組織“賈哈林之友”的雅埃爾·莫阿茲 (Yael Moaz) 詢問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支持和包容他們。 村里的領導艾德·賈哈林 (Eid Jahalin) 說:“你應該為婦女們做點什麼。” 起初,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會是什麼樣子。 但期間 穆什基萊,居民經常對自己的經濟邊緣化表示沮喪。 附近的定居點過去曾僱用他們,政府也曾向他們發放進入以色列的工作許可證,但這一切都因他們的激進主義而停止。 當他們工作時,幾乎沒有錢。
活動人士向這些女性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知道該怎麼做嗎?” 有一位老婦人記得如何製作帳篷,但刺繡是大多數婦女已經失去的一項文化技能。 首先,婦女們說她們不會刺繡。 但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想起來了——他們模仿了自己的刺繡衣服,並提出了自己的娃娃設計。 一些女性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學會了,並開始告訴加利亞·柴(Galya Chai)——一位設計師,也是去年夏天幫助為阿馬爾汗守夜的以色列女性之一——要帶什麼樣的繡線。
一個名為“盧埃巴·赫魯瓦,“ 要么 漂亮娃娃,正是在這種努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在每個月從遊客、遊客、活動人士和他們的朋友那裡帶來幾百謝克爾的收入——對居民的生活質量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 這些娃娃還在以色列各地的進步活動場所出售,例如 因巴拉咖啡館 在耶路撒冷。 由於供應量超過了當地的需求,他們現在正尋求在伯利恆等其他地方以及國際上銷售這些娃娃。

在一個即將被以色列政府從地圖上抹去的村莊里,柴解釋了他們如何解決明顯的權力失衡問題。 “我們通過長期努力贏得了信任,”她說。 “去年夏天有很多人,來過一次兩次,但很難一直參與其中。 我們是唯一真正這樣做的人。 我們每個月去那里二、三、四次。 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就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他們很高興見到我們,現在這是私人的事情。”
該項目在沒有任何正式資金的情況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他們已經開始了 Instagram 從女性自己的角度來說——她們對被拍照感到不舒服,但村莊本身、孩子們和她們的雙手卻可以。 他們舉辦了一場有 150 名參觀者參加的活動,並正在考慮舉辦更多大型活動。 “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因為他們感覺很遙遠,”柴解釋道。 “每個娃娃都帶有一條信息,講述著這個村莊。 上面有製造商的名字。”
婦女們正在考慮帶更多的團體到村里學習刺繡藝術。 沒有兩個娃娃是一樣的。 “這些娃娃開始看起來像製作它們的人,”柴笑著說。 “這個娃娃和它的身份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有更年輕的女孩,比如15歲的女孩,她們非常有才華,而且娃娃看起來更年輕。 它們開始看起來像它們的製造者。”
該項目正在不斷發展,歡迎任何人加入。 目前約有 30 名娃娃製作者,其中包括十幾歲的女孩。 他們各自工作,但每個月都有幾次集體聚會。 該項目已發展成為一項更大的努力,旨在解決嚴肅的問題、資源重新分配和自我引導的解放組織。 例如,老年婦女有視力問題,因此以色列婦女開車送她們去看耶路撒冷的一位提供免費服務的驗光師。 婦女們現在有興趣學習如何使用縫紉機縫製衣服。 有時他們想做陶瓷,所以以色列人會帶來粘土。 有時他們會說,開著車來,我們去野餐吧。

柴謹慎地表示,“我們不僅帶來和做事,他們也為我們做事。 他們總是想給我們一些東西。 有時他們給我們做麵包,有時他們給我們泡茶。 上次我們去那裡時,一位女士為她做了一個洋娃娃,上面寫著她的名字加扎拉。” 她的名字叫 Yael,聽起來像 加扎拉, 阿拉伯語中羚羊的意思。 當一些以色列人了解這個項目時,他們建議向婦女們傳授一些東西。 但 Chai 對這個項目的正義鏡頭很堅定——她不是來發起或讓事情看起來像某種方式的,而是共同設計。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深思熟慮,不要咄咄逼人,不要成為‘以色列人’。”
明年,安拉
我用手撫過玩偶複雜的縫線,聞到了堅硬泥土的氣味,這種氣味早在軍事佔領之前就存在,而且在軍事佔領之後也將長期存在。 有人提醒我,文化記憶和復興是一種重要的抵抗形式,就像莎拉竭盡全力將自己的身體從警察手中解放出來一樣重要,或者數百名活動人士在汗·阿馬爾被圍困的學校裡堅持四個月的靜坐一樣重要。
這家人顯然很懷念國際遊客的存在和團結。 當我們準備離開時,烏姆·伊斯梅爾告訴我,我必須盡快回來看望汗·阿馬爾,並帶上我的丈夫。 “明年, 因沙拉,”這是我能給出的最誠實的答案。 我們都知道以色列政府完全有可能兌現其承諾,並在明年之前摧毀阿馬爾汗號。 但就目前而言,人民的力量佔了上風。 我問莎拉和她的母親是否認為 穆什基萊 如果武裝部隊、推土機和拆除工作能夠回歸的話,這種情況將會繼續下去。 “當然,”烏姆·伊斯梅爾若有所思地說。 “我們是巴勒斯坦人。” 我們都強忍著悲傷的微笑,默默地喝著茶。 我們一起看著夕陽西下,映入看似無邊無際的沙漠山丘中。
Sarah Flatto Manasrah 是一位倡導者、組織者、作家和助產士。 她的工作重點是性別、移民、難民司法和暴力預防。 她住在布魯克林,但花了很多時間在聖地喝茶。 她是一個穆斯林、猶太、巴勒斯坦、美國家庭的驕傲成員,這個家庭有四代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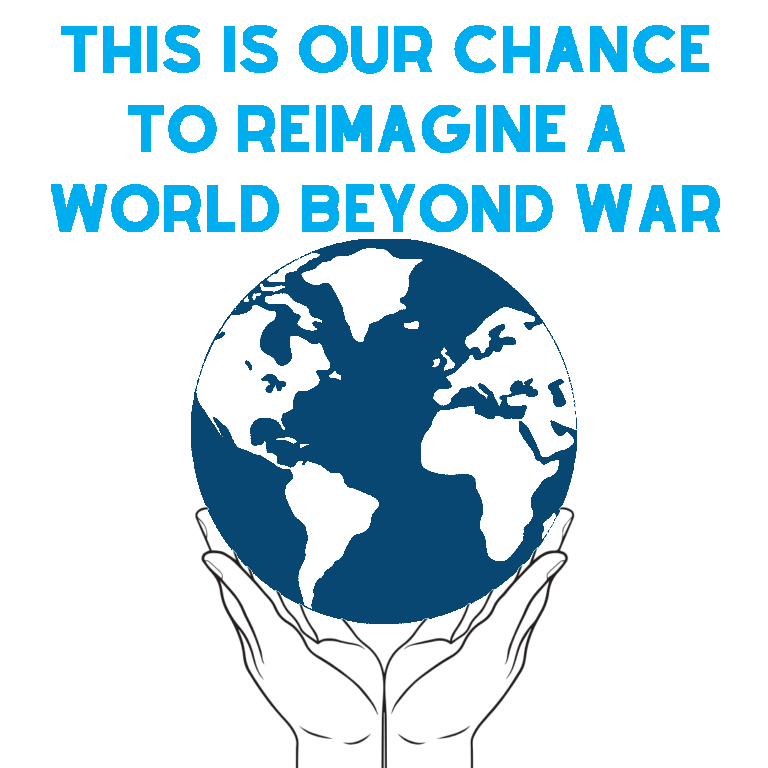







3回應
任何村莊都不會被摧毀!
2018 年,我有幸與無數巴勒斯坦和國際合作夥伴一起支持勇敢的汗阿馬爾人民。 該村莊沒有被以色列人完全夷為平地,這一事實證明了不懈的堅持、保護性的非暴力配合和持續的法律上訴的力量。
這是非暴力抵抗、和平共處和建立友誼紐帶的力量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船在世界熱點之一。 以色列人明智的做法是放棄他們的主張並允許該村莊繼續生存並代表以色列 World Beyond War 這個星球上大多數居民都渴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