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女演員或者一個演員和狗
凱倫·馬爾佩德
我正在和我的狗赫爾墨斯交談。 他躺在我桌子旁邊的地板上。
“卡倫,”赫姆說。 他發“r”音有困難,說話帶有輕微的口音,肯定是可卡犬的口音。 “為什麼人們不能,undewhrstrand?”
“我不知道,赫姆,”我說。 我發現我經常這樣回答他的問題。
他又開始輕輕地舔著左爪。
“你還記得以前的日子嗎?”
“赫姆,你在說什麼?”
“你的日子,卡倫。 (停頓) 之前……”
他轉身梳理自己的右爪。 赫姆有一雙令他非常自豪的大腳。 梳洗完畢後,他伸了個懶腰,在地毯上表演了上犬式和下犬式,搖晃著自己的故事,以表彰他完美的體形。 然後他抬頭看著我。
“當你年輕的時候。” 他說。
“哦,是的,我記得,赫姆,”我說。 “我曾經騎著自行車沿著街道兩旁種滿了老榆樹,這些老榆樹的樹枝相互接觸,在我的頭頂上形成了一個天篷。 那是在荷蘭榆樹病之前。”
“為什麼有人會傷害兩棵樹?” 赫姆驚愕地問道。
“你在樹上撒尿,”我提醒他。
“只有大樹,卡倫,絕對不能在小樹上撒尿。”
赫爾墨斯躺下; 他的兩條後腿張開,頭枕在爪子上。
我曾經騎馬走進密林深處。 我常常獨自一人出去,沒有馬鞍,除了我和我的馬,沒有其他人,有時是在晚上,在月光下,但最常見的是在中西部炎熱的夏日。 從涼爽的樹林中出來,我們來到了一片圓形的小草地,周圍有樹蔭和庇護。 我會滑下他溫暖的肌膚,將臉頰靠在他的脖子上。 我會躺下來,我的馬在我身邊吃草,我的眼睛平視地面,凝視著這個微型世界。 優雅的長頸昆蟲帶著精緻蝕刻的透明風,在細長的腿上平衡,在因重量而彎曲的細長草葉上,來回嘰嘰喳喳。 忙碌的螞蟻承擔著兩倍大的負擔。 蠕蟲浮出水面並潛水。 蜘蛛編織半透明的網。 蜜蜂飛來飛去,喝水。 紅雀翅膀,這些詞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就像舌頭上的許多大自然的名字一樣美麗。 凝視著草地上的草和蟲子的微型世界,與孩子的腹部壓在地上的高度齊平,這就是仙女世界和童話故事的開始。
“卡倫,”赫姆說道,現在進入了他的演講重點,“你年輕時從未想過人們會傷害這個世界!”
“永遠不會,赫姆。” 那不是真的。 我還是個孩子,正值冷戰最糟糕的日子; 我們認為核武器會毀滅世界。 我的世界在秘密草地上,花斑在我身邊吃草,快要被炸得四分五裂了。 現在,我們看著冰融化並等待……但從這些想法來看,我可以保護我的狗。
“我永遠不會傷害,”赫爾墨斯說。
“好吧,你吃生牛肉和雞肉,赫姆。”
“還有披薩餅皮,”他說。
“來自街上,噁心”
“沒有人是完美的,卡倫,”赫姆回答道。 “我們每個人都受到了妥協。”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站起來,強調道,“我們不應該扭扭捏捏。 我們以各種方式都知道。” 他把下巴擱在我腿上。 “我努力做一隻好狗。”
“這是真的,赫爾墨斯,”我揉著他的頭說,“你是我認識的最好的狗。” 與我深愛的他的妹妹克萊斯不同,赫耳墨斯普遍善良、友善且聽話。
“克萊斯不說話,”赫姆說,讀懂了我的心思。
“確實如此,赫爾姆,”我回答道,儘管赫爾墨斯在我的腦海裡對我說話,而我必須為他說話,克萊斯,無論我多麼努力地聽,仍然堅決保持沉默。 我聽不到她的聲音。 當克萊斯想成為一個孩子時,就像在公園裡一樣,她會閉上耳朵,不聽我的聲音,鼻子貼著地面,繞著大圈跑,自由而野性。 我在她身後呼喚,愚蠢地追她。 我用餅乾求她。 當她累了的時候,她就會坐下來。
我有一位馬術老師曾經說過,“他們告訴我馬是不會說話的動物,但我想知道”,他指的是我們這些努力與兩腿之間的數千磅肉進行交流而不被立即扔掉的人。
“卡魯恩,”赫姆說,“為什麼人們這麼笨?”
他現在很生氣。
為了進一步強調,他咆哮道。 克萊斯也叫了一聲。 然後,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它們的叫聲越來越快,直到一起瘋狂地、放縱地嚎叫。
刺耳的聲音一停止,赫爾墨斯就挺直了身子。 前腿落地,後腿伸展,頭抬起。 他語氣嚴肅地說:“我們的世界很美麗。 我們只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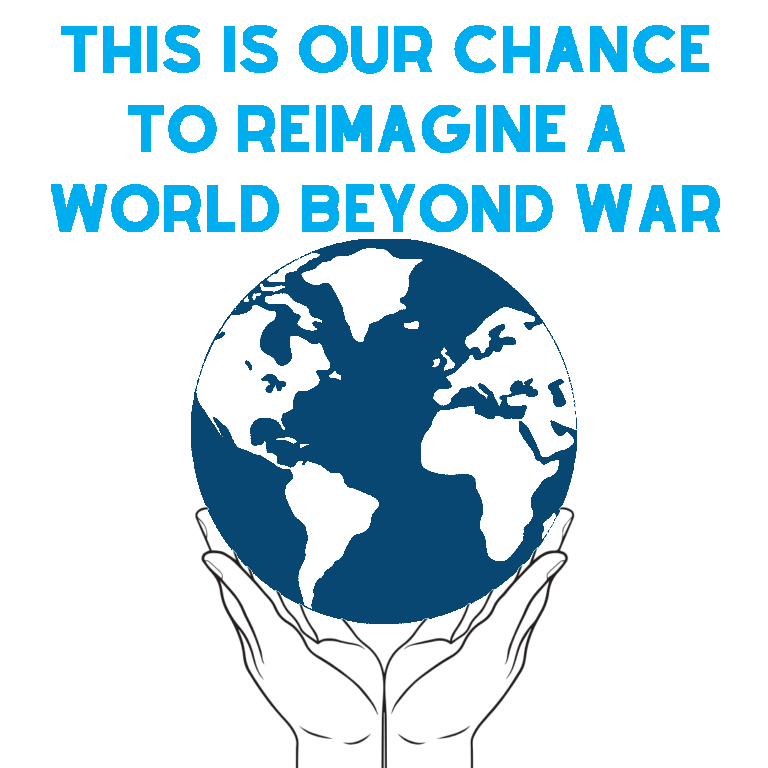







一個響應
凱倫,多虧赫爾墨斯和克萊斯,繆斯女神又回來了。 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