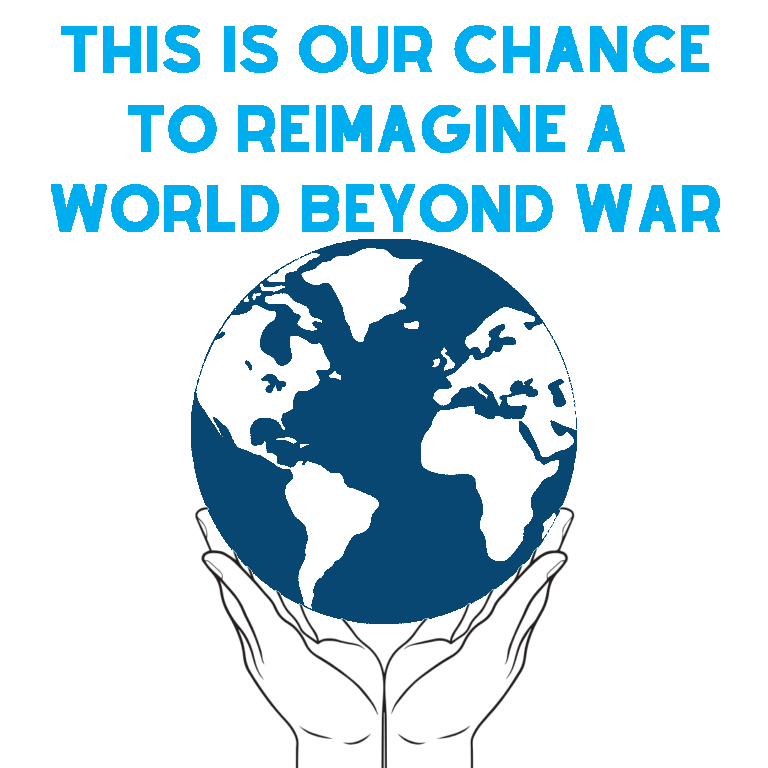作者:戴夫·艾格斯, 守護者.
Inder Comar 是一位舊金山律師,他的通常客戶都是科技初創公司:他能否對 2002 年戰爭的策劃者提起唯一的訴訟?

上訴法院大樓外的因德爾科馬爾。 攝影:Winni Wintermeyer 為《衛報》拍攝
原告是桑杜斯·沙克·薩利赫 (Sundus Shaker Saleh),一名伊拉克教師、藝術家和五個孩子的母親,被迫離開 伊拉克 在入侵之後,該國隨後陷入內戰。 她的家人在約旦安曼一度富裕,但自 2005 年以來一直生活在貧困之中。
薩利赫的代表是一位 37 歲的律師,他獨自工作,通常的客戶都是尋求保護知識產權的小型科技初創公司。 他的名字是 因德爾科馬爾, 而如果 阿迪克斯芬奇 如果科馬爾被重新塑造成一位富有鬥志的、多元文化的西海岸律師,他的母親是墨西哥人,父親來自印度,也許就足夠了。 他很英俊,很容易微笑,儘管在那個大風的星期一站在法院外,他很緊張。 目前尚不清楚新套裝是否有幫助。
“我剛剛得到它,”他說。 “你怎麼認為?”
這是一件三件套,銀灰色,帶有黑色細條紋。 科馬爾幾天前買了它,認為他需要看起來盡可能專業和理智,因為自從他想到起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的想法以來,他一直意識到不要顯得是個瘋子或外行。 但這套新套裝的影響卻很模糊:它要么是狡猾的德克薩斯石油商穿的那種衣服,要么是被誤導的青少年在舞會上穿的衣服。
前一天,在科馬爾的公寓裡,他告訴我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聽證會。 他從未在第九巡迴法院(僅比最高法院低一級)辯論過任何案件,而且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正常吃飯、睡覺或鍛煉了。 “我仍然對我們舉行聽證會感到震驚,”他說。 “但這已經是一場胜利,美國法官將聽取並辯論這一點。”
要點是:總統、副總統和其他策劃戰爭的人是否對其後果負有個人法律責任。 通常,行政部門不會受到與在任期間採取的行動有關的訴訟,所有聯邦僱員也是如此; 但這種保護僅適用於這些僱員在其僱傭範圍內行事的情況。 科馬爾認為布什等人的行為超出了這種保護範圍。 此外,他們還犯下了侵略罪——違反了國際法。
幾個小時後,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將同意科馬爾的觀點,並要求戰爭策劃者——前總統 喬治W布什, 前副總統 理查德·B·切尼,前國務卿 科林·鮑威爾,前國防部長 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前國防部副部長 保羅·沃爾福威茨 和前國家安全顧問 賴斯 ——對伊拉克的內爆、超過 500,000 萬伊拉克平民死亡和 XNUMX 萬人流離失所負責,這似乎是極不可能的。
“話又說回來,”科馬爾說,“也許他們只是想,‘為什麼不讓這個人在法庭上待上一天呢?’”
***
戰爭爆發時,因德爾·科馬爾正在紐約大學法學院就讀,雖然入侵從壞到好,再到壞到災難,他選修了一門關於國際法中無端侵略的課程,該課程以美國製定的法律先例為中心。 紐倫堡法庭。 在紐倫堡,檢察官成功地辯稱,儘管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領導人是在德國國家管理者的職責範圍內執行命令並行事的,但他們仍然應對侵略罪和反人類罪負責。 納粹無緣無故地入侵主權國家,無法利用國內法來保護它們。 羅伯特·傑克遜在開幕詞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兼首席檢察官表示:“這次審判代表了人類不顧一切的努力,要對那些利用國家權力攻擊世界和平基礎、侵犯權利的政治家施加法律紀律。”他們的鄰居。”
在科馬爾看來,這個案子至少有一些重疊之處,特別是在全世界意識到之後 薩達姆·侯賽因 民政事務總署 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入侵的策劃者早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概念出現之前就已經考慮了伊拉克的政權更迭。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國際輿論開始聯合起來反對戰爭的合法性。 2004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 科菲·安南稱這場戰爭“非法”. 荷蘭議會稱此舉違反國際法。 在2009, 本傑明·費倫茨紐倫堡的一位美國檢察官寫道,“可以提出一個很好的論據,證明美國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

科馬爾當時是一名在舊金山執業的私人律師,他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起訴政府。 外國公民可以在美國就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提起訴訟,因此,考慮到伊拉克戰爭受害者的法律地位和紐倫堡審判所開創的先例,科馬爾認為確實有可能提起訴訟。 他向其他律師和前教授提到了這一點。 有些人有點鼓勵,但沒有人認為這樣的套裝會派上用場。
與此同時,科馬爾半期待其他人來起訴此案。 美國有超過 1.3 萬律師和數千個積極進取的非營利組織。 一些訴訟已經提起,認為這場戰爭從未得到國會的適當授權,因此是違憲的。 拉姆斯菲爾德因批准對被拘留者使用酷刑而提起了十幾起訴訟。 但沒有人認為,當他們策劃和執行戰爭時,行政部門違反了法律。
***
2013 年,科馬爾在一個名為 The Hub 的共享辦公空間工作,周圍都是初創公司和非營利組織。 他的一位同事認識了一個居住在海灣地區的約旦顯赫家族,自戰後以來,他們一直在幫助安曼的伊拉克難民。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將科馬爾介紹給了居住在約旦的難民,其中包括桑杜斯·沙克爾·薩利赫 (Sundus Shaker Saleh)。 科馬爾和薩利赫通過 Skype 進行交談,他在她身上發現了一位熱情而雄辯的女性,在入侵 12 年後,她仍然感到憤怒。
薩利赫 1966 年出生於巴格達卡赫。她在巴格達藝術學院學習,成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家和教師。 薩利赫家族是薩比曼迪安信仰的信徒,該宗教遵循施洗者約翰的教義,但在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領域之外擁有一席之地。 儘管戰前伊拉克境內的曼迪人不到100,000萬,但侯賽因卻對他們置之不理。 無論他犯了什麼罪,他都維持了伊拉克許多古老信仰和平共處的環境。
美國入侵後,秩序消失,宗教少數群體成為目標。 薩利赫成為一名選舉官員,她和她的家人受到威脅。 她遭到襲擊,並向警方尋求幫助,但警方表示他們無法保護她和她的孩子。 她和她的丈夫分居了。 他帶著他們的大兒子,她帶著全家的其他人去了約旦,他們自 2005 年以來一直居住在那裡,沒有護照或公民身份。 她當過女傭、廚師和裁縫。 她12歲的兒子不得不輟學去打工,為家庭做出貢獻。
2013年XNUMX月,薩利赫聘請科馬爾對入侵伊拉克的策劃者提起訴訟; 他不會收到任何錢,也不會尋求賠償。 五月,他前往約旦聽取她的證詞。 “我多年來建造的東西在我眼前在一分鐘內被摧毀了,”她告訴他。 “我的工作、我的職位、我的父母、我的整個家庭。 現在我只想活下去。 作為母親。 我的孩子們就像一朵花。 有時我無法給它們澆水。 我喜歡抱著它們,但我太忙於生存了。”
***
“現在是危險的時期,”科馬爾去年 11 月 25 日告訴我。 他本來沒有計劃就特朗普提出自己的觀點,但他的第一次聽證會是在選舉一個月後舉行的,濫用權力的影響是嚴重的。 科馬爾的案件涉及法治——國際法、自然法——而特朗普並沒有表現出對程序或事實的深深尊重。 事實是伊拉克戰爭的核心。 科馬爾認為,這些信息是為了為入侵辯護而炮製出來的,如果有哪位總統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偽造事實,那一定是特朗普,他在推特上向他的XNUMX 萬粉絲發布了明顯虛假的信息。 如果有一個時間來澄清美國在入侵主權國家方面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那麼現在似乎就是了。
對於科馬爾來說,第二天聽證會的最佳結果是法院將案件送交證據聽證會:進行適當的審判。 然後他必須準備一個實際案件——規模與紐倫堡法庭本身相當。 但首先他必須通過《西部荒野法案》。
《西部荒野法案》的全稱是《1988 年聯邦僱員責任改革和侵權賠償法案》,它是科馬爾訴訟和政府辯護的關鍵。 從本質上講,該法案保護聯邦僱員免受因其職責範圍內的行為而引起的訴訟。 如果郵政工作人員無意中投遞了炸彈,他或她不能在民事法庭上被起訴,因為他們是在其工作範圍內運作的。
當原告因拉姆斯菲爾德使用酷刑而起訴拉姆斯菲爾德時,就適用了該法案。 不過,在每一個案件中,法院都同意用美國代替他作為指定被告。 隱含的推理是拉姆斯菲爾德作為國防部長的任務是保衛國家,並在必要時規劃和執行戰爭。

“但這正是紐倫堡法庭所解決的問題,”科馬爾告訴我。 “納粹也提出了同樣的論點:他們的將軍肩負著發動戰爭的任務,他們也這樣做了,他們的士兵也聽從了命令。 這就是紐倫堡駁斥的論點。”
科馬爾住在舊金山市中心的一間單間公寓裡,過著近乎斯巴達式節儉的生活。 景色是一堵長滿青苔和蕨類植物的水泥牆。 浴室很小,訪客可以在門廳洗手。 他床邊的書架上有一本書,書名是 吃大魚.
他不必這樣生活。 法學院畢業後,科馬爾在一家公司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四年,負責知識產權案件。 他離開公司創建了自己的公司,這樣他就可以將時間分配在社會正義案件和支付賬單的案件上。 畢業十二年後,他仍然背負著法學院貸款的巨額債務(就像 奧巴馬 當他上任時)。
當我們 18 月份談話時,他還有許多其他緊迫的案件,但已經為聽證會準備了近 XNUMX 個月。 當我們談話時,他不斷地望向窗外,看向苔蘚牆。 當他微笑時,他的牙齒在平面燈光下閃閃發光。 他很認真,但很快就笑了,喜歡討論想法,經常說:“這是個好問題!” 他的外表和說話都像他典型代表的科技企業家:深思熟慮、冷靜、好奇,還有一點“為什麼不嘗試一下?”的感覺。 態度對於任何初創公司都至關重要。
自 2013 年首次提起訴訟以來,科馬爾的案件一直在下級法院審理,官僚作風似乎毫無結果。 但中間的時間給了他機會來證實他的想法。 當他向第九巡迴法院提起上訴時,他意外地得到了八位著名律師的支持,每一位律師都添加了自己的法庭之友陳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拉姆齊·克拉克,美國前司法部長 林登·約翰遜和馬喬裡·科恩,前總統 全國律師協會。 隨後,科馬爾收到了他曾寫信給 97 歲的紐倫堡檢察官本傑明·費倫茨 (Benjamin Ferencz) 創建的基金會的來信:星球基金會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陳述。
“這些簡報意義重大,”科馬爾說。 “法庭可以看到這背後有一支小軍隊。 這不僅僅是舊金山的某個瘋子。”
***
12 月 7 日星期一寒冷且有大風。 舉行聽證會的法庭位於 Mission Street 和 30th Street,距離公開購買和消費毒品的地方不到 XNUMX 米。 與 Comar 一起是 柯蒂斯·多布勒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法學教授; 他前一天晚上飛過。 他留著鬍子,戴著眼鏡,很安靜。 他穿著長長的深色風衣和厚重的眼瞼,給人一種從霧濛濛的夜晚帶著壞消息走出來的感覺。 科馬爾打算給他 15 分鐘中的 XNUMX 分鐘時間,從國際法的角度關注此案。
我們八點半進入法庭。 上午的所有上訴人預計在九點前到達並恭敬地聽取上午其餘的案件。 法庭很小,大約有30個座位,供旁聽者和參與者使用。 評委席很高,由三人組成。 三位評委每人都有一個麥克風、一小壺水和一盒紙巾。
面對法官的是律師陳述論點的講台。 它是光禿禿的,但有兩個物體:一張印有評委名字的紙——赫爾維茨、格雷伯和博爾韋爾——以及一個鬧鐘大小的裝置,上面有三個圓形的燈:綠色、黃色、紅色。 時鐘的數字顯示設置為 10.00:0。 這是計時器,倒數到 XNUMX,它會告訴 Inder Comar 他還剩多少時間。
解釋第九巡迴法庭聽證會的含義和不含義非常重要。 一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法院,其法官備受尊敬,並且在選擇審理的案件時非常嚴格。 另一方面,他們不審理案件。 相反,他們可以維持下級法院的裁決,或者可以將案件發回重審(將其發回下級法院進行真正的審判)。 這就是科馬爾所尋求的:就戰爭合法性舉行實際聽證會的權利。
第九巡迴法庭的最後一個關鍵事實是,它為每個案件每方分配 10 到 15 分鐘的時間。 原告有 10 分鐘的時間解釋為什麼下級法院的裁決是錯誤的,被告有 10 分鐘的時間解釋為什麼先前的裁決是公正的。 在某些情況下,表面上當某個問題特別重要時,案例會被給予 15 分鐘的時間。
卡拉 OK 案以及當天上午的其他案件中的原告被給予了 10 分鐘的時間。 科馬爾和薩利赫的案例已被給出15。這至少是對當前問題的相對重要性的粗略認可:美國是否可以以虛假藉口入侵主權國家的問題——其先例和影響。
話又說回來,大力水手雞案也被給予了 15 分鐘的時間。
***
當天的訴訟開始了,對於任何沒有法律學位的人來說,科馬爾面前的案件沒有多大意義。 律師沒有提供證據、傳喚證人和交叉詢問。 相反,每次調用案例時,都會發生以下情況。 律師走上講台,有時轉向觀眾,尋求同事或親人最後的勇氣。 然後律師將他或她的文件帶到講台上並仔細整理。 在這些頁面上——當然在科馬爾的頁面上——是律師將要說的話的書面大綱,整潔,經過深入研究。 文件整理好後,律師表示已準備就緒,書記員啟動計時器,10.00 點很快變成 8.23 和 4.56,然後是 2.00 點,此時綠燈變為黃燈。 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傷腦筋的。 時間不夠。
而這一切時間都不屬於原告。 無一例外,前90秒內,評委們猛撲。 他們不想听演講。 他們閱讀了案情摘要並研究了案例; 他們想深入了解它的本質。 對於未經訓練的人來說,法庭上發生的大部分事情聽起來都像是詭辯——測試法律論證的強度,提出和探索假設,審查語言、語義和技術細節。

評委們的風格截然不同。 左邊的安德魯·赫維茨 (Andrew Hurwitz) 發言最多。 他的面前是一個高高的杯子 赤道 咖啡; 在第一個案件中,他完成了它。 此後,他似乎嗡嗡作響。 當他打斷律師的發言時,他不斷地、條件反射地轉向其他法官,彷彿在說:“我說得對嗎? 我對嗎?” 他似乎很開心,微笑著,咯咯笑,總是很投入。 他曾一度引用 宋飛說, “沒有湯給你喝。” 在卡拉 OK 案件中,他表示自己是一名卡拉 OK 愛好者。 “我是卡拉 OK 的消費者,”他說。 然後他轉向另外兩位法官,彷彿在說:“我說得對嗎? 我對嗎?”
中間的蘇珊·格雷伯法官沒有回應赫維茨的目光。 在三個小時的大部分時間裡,她一直直視前方。 她皮膚白皙,臉頰紅潤,但感情卻很嚴重。 她的頭髮很短,眼鏡很窄;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俯視著每一位律師,她的嘴幾乎處於驚愕的邊緣。
右邊是理查德·布爾韋爾法官,年輕,非裔美國人,留著修剪整齊的山羊胡。 他是指定席位,這意味著他不是第九巡迴法院的永久成員。 他時不時地微笑,但就像格雷伯一樣,他會抿起嘴唇,或者把手放在下巴或臉頰上,這表明他幾乎無法忍受眼前的胡言亂語。
臨近十一點,科馬爾變得更加緊張。 11 點 11.03 分,書記員宣布:“Sundus Saleh v 喬治·布什,”很難不為他和他簡潔的兩頁大綱感到焦慮。
綠燈亮了,Comar 開始了。 他只說了一分多鐘,就被格雷伯打斷了。 “讓我們切入正題吧,”她說。
“當然,”科馬爾說。
“當我讀到這些案例時,”她說,“聯邦僱員的行為可能是非常錯誤的,但仍然受到《西部荒野法案》的保護,仍然是他們就業的一部分,因此受到《西部荒野法案》的豁免。 你不同意這個一般原則嗎?”
“作為一般原則,我並不反對這一點,”科馬爾說。
“好吧,”格雷伯說,“那麼這個特殊的東西有什麼不同呢?”
當然,這就是科馬爾想說的地方:“這件事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一場戰爭。 一場基於虛假藉口和捏造事實的戰爭。 一場造成至少五十萬人死亡的戰爭。 五十萬靈魂,一個國家被毀滅。” 但在最激動的時刻,他的神經混亂了,他的大腦陷入了法律的束縛,他回答說:“我認為我們需要深入了解華盛頓法律的雜草,看看華盛頓法律的案例,其中... ...”
赫維茨打斷了他,從那裡開始,三位法官互相打斷對方和科馬爾,但主要是關於《西部荒野法案》以及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是否在他們的工作範圍內行事。 有幾分鐘的時間,它是滑稽地簡化的。 赫爾維茨一度詢問,如果任何被告受傷,他們是否會獲得工人賠償。 他的觀點是,總統和他的內閣都是政府僱員,了解這份工作的福利和豁免權。 這種討論符合當今大部分時間的模式,其中假設是有趣的,主要是出於有趣的腦筋急轉彎的精神,比如填字遊戲或國際象棋遊戲。
九分鐘後,科馬爾坐下來,將接下來的五分鐘讓給了多布勒。 就像一個替補投手在對手的擊球陣容中取得新的突破一樣,多布勒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開始,並且第一次提到了戰爭的後果:“這不是你慣常的侵權行為,”他說。 “這一行動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我們不是在談論政府官員是否僅僅在他的工作期限內、在他的辦公室內做了一些可能造成一些損害的事情……”
“讓我阻止你一下,”赫爾維茨說。 “我想了解你所提出的論點有何不同。 你的同事說我們不應該找到適用的《西部荒野法案》,因為他們沒有在他們的工作範圍內行事。 讓我們假設他們暫時存在。 你是否在說,即使是,《西部荒野法案》也不適用?”
多布勒的五分鐘很快就過去了,接下來就輪到政府了。 他們的律師大約30歲,身材瘦長,精神鬆散。 當他反駁科馬爾的論點時,他似乎一點也不緊張,幾乎完全是根據《西部荒野法案》。 他有 15 分鐘的時間為政府辯護,反對非正義戰爭的指控,但他只用了 11 分鐘。
***
當第九巡迴法院於 9 月 XNUMX 日裁定特朗普的旅行禁令無效時,許多美國媒體,當然還有美國左翼人士,都慶祝了 法院願意加強並製衡總統權力 具有生硬的司法常識。 特朗普入主白宮從第一天起就表現出強烈的單邊行動傾向,而共和黨國會站在他一邊,只剩下司法部門來限制他的權力。 第九巡迴法院正是這樣做的。
唐納德·特朗普 (@realDonaldTrump)
法庭見,我們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
第二天,第九巡迴法院最終對薩利赫訴布什案做出了裁決,但在這裡他們卻做了相反的事情。 他們確認行政部門享有豁免權,無論犯罪規模如何。 他們的意見中包含這樣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句子:“當《西部荒野法案》通過時,很明顯這種豁免權甚至涵蓋了令人髮指的行為。”
該意見長達 25 頁,解決了科馬爾投訴中提出的許多觀點,但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法院一次又一次地遵循《西部荒野法案》,並否認任何其他法律取代它——甚至包括禁止侵略的多項條約,包括 聯合國憲章。 該意見為證明其服從是合理的,但提供了一個可能不受法律管轄的犯罪行為的例子:“例如,如果一名聯邦官員利用他的影響力,他就會出於‘個人’動機行事。為配偶的生意謀取利益,而不顧由此對公共福利造成的損害。”
“這是對特朗普的提及,”科馬爾說。 這意味著,實施非正義戰爭是不可起訴的; 但如果現任總統利用他的辦公室來幫助 梅拉尼亞例如,法院可能對此有話要說。
***
這是裁決後的第二天,科馬爾坐在他的公寓裡,仍在處理案件。 早上收到意見,直到下午才有精力看; 他知道這對他不利,這個案子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薩利赫目前作為尋求庇護者居住在第三國,並處理健康問題。 她已經筋疲力盡,生活中沒有更多的空間去打官司。
科馬爾也很累。 此案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才到達第九巡迴法院。 他小心翼翼地表達了對法庭首先聽取了這件事的感激之情。 “好消息是他們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他們確實解決了每一個爭論。”
他嘆了口氣,然後列舉了法庭沒有解決的問題。 “他們有權審視國際法並承認侵略是強制法規範。” 換句話說,第九巡迴法院本可以將非法戰爭視為“最高”犯罪,就像紐倫堡法官所做的那樣,並接受不同程度的審查。 “但他們沒有。 他們說,“我們可以這樣做,但我們今天不會這樣做。” 根據這項裁決,白宮和國會可以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實施種族滅絕,並受到保護。”
案子結束後,科馬爾計劃好好睡覺和工作。 他正在完成與一家科技公司的收購交易。 但他仍然對裁決的影響感到不安。 “我真的很高興法院在移民問題上挑戰特朗普。 但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當談到戰爭與和平時,在美國,它只是被困在我們大腦的另一部分。 我們只是不質疑它。 我們需要談談為什麼我們總是處於戰爭狀態。 以及為什麼我們總是單方面這樣做。”
科馬爾說,布什政府在沒有對個人造成任何後果的情況下發動了這場戰爭,這一事實不僅讓特朗普更加膽大妄為,而且還讓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為更加大膽。 “俄羅斯人以伊拉克為藉口[他們的入侵] 克里米亞。 他們和其他人以伊拉克為先例。 我的意思是,我們建立的條約和憲章建立了一個機制,如果你想從事暴力,你必須合法地這樣做。 你必須得到聯合國的決議並與你的伙伴合作。 但整個系統正在瓦解——這使得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