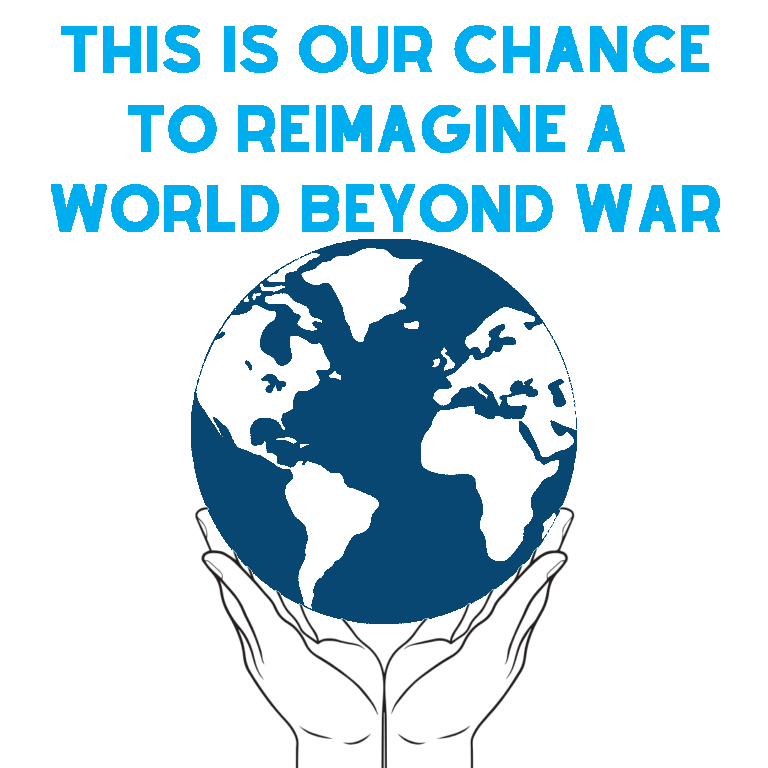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越南和敘利亞,毒品往往與炸彈和子彈一樣成為衝突的一部分。

芭芭拉·麥卡錫, 半島電視台
阿道夫·希特勒是個癮君子,納粹的吸毒行為給“毒品戰爭”一詞賦予了新的含義。 但他們並不是唯一的人。 最近的出版物顯示,毒品與子彈一樣是衝突的一部分。 經常定義戰爭,而不是袖手旁觀。
在他的書 發起猛攻德國作家諾曼·奧勒描述了第三帝國如何充斥著毒品,包括可卡因、海洛因,尤其是冰毒,從士兵到家庭主婦和工廠工人,每個人都使用冰毒。
最初以德文出版為 勞施的全部 該書詳細介紹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隨者的虐待歷史,並發布了有關西奧多·莫雷爾博士之前未發表的存檔調查結果,西奧多·莫雷爾博士是一位私人醫生,曾向德國領導人以及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服用藥物。
“希特勒吸毒也是元首。 考慮到他極端的個性,這是有道理的。”奧勒在柏林的家中說道。
去年奧勒的書在德國出版後,《法蘭克福匯報》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 題:“當你將希特勒視為癮君子時,他的瘋狂行為是否會變得更容易理解?”
“是的,也不是,”奧勒回答道。
希特勒的精神和身體健康狀況引起了很多猜測,他每天都要注射“神藥”優可多(Eukodol)和可卡因(它能讓使用者處於欣快感狀態,並且常常使他們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可卡因,他從 1941 年開始定期服用可卡因來治療慢性胃痙攣、高血壓和耳膜破裂等疾病。
“但我們都知道他在那之前做了很多可疑的事情,所以你不能把一切都歸咎於毒品,”奧勒反思道。 “話雖如此,他們確實在他的死亡中發揮了作用。”
奧勒在他的書中詳細描述了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藥物如何讓最高指揮官在他的妄想中保持穩定”。
他寫道:“他周圍的世界可能會化為廢墟和灰燼,他的行為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但當他人為的欣喜感開始出現時,元首感到更加合理。”
奧勒解釋說,但上升必然下降,當戰爭接近尾聲時,供給耗盡,希特勒忍受著嚴重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戒斷、偏執、精神病、爛牙、極度顫抖、腎衰竭和妄想等症狀。
在元首地堡的最後幾周里,他的精神和身體每況愈下, 地下 奧勒說,納粹黨成員的庇護所可以歸因於退出尤科多爾,而不是像以前認為的那樣是帕金森氏症。
 |
二戰
當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納粹提倡雅利安人清潔生活的理想,但他們自己卻一點也不干淨。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毒品在德國首都很容易買到, 柏林。 但 1933 年奪取政權後,納粹將其宣佈為非法。
然後,在 1937 年,他們為基於甲基苯丙胺的藥物申請了專利 珀維丁– 一種興奮劑,可以讓人們保持清醒並提高他們的表現,同時讓他們感到欣快。 他們甚至還生產了一個品牌的巧克力, 希爾德布蘭德,其中含有 13 毫克藥物——比普通的 3 毫克藥丸多得多。
1940 年 XNUMX 月,超過 35萬元 在入侵法國期間,來自柏林 Temmler 工廠的 3 毫克劑量的 Pervitin 被運往德國軍隊和德國空軍。
“士兵們連續幾天醒著,不停地行進,如果沒有冰毒,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所以是的,在這種情況下,毒品確實影響了歷史,”奧勒說。
他將納粹在法國戰役中的勝利歸功於毒品。 “希特勒對戰爭毫無準備,他已陷入絕境。 國防軍的實力不如盟軍,裝備也很差,而且與盟軍的四百萬士兵相比,他們只有三百萬士兵。”
但帶著 Pervitin 的裝備,德國人在 36 到 50 個小時不眠不休的情況下,穿越了困難的地形。
戰爭快結束時,當德國人節節敗退時,藥劑師格哈德 奧爾澤霍夫斯基 發明了一種可卡因口香糖,可以讓單人潛艇的飛行員連續幾天保持清醒。 許多人因長期隔離在封閉空間內服用藥物而精神崩潰。
但當生產 Pervitin 和 Eukodol 的 Temmler 工廠被 轟炸 1945 年,盟軍簽署了該法案,標誌著納粹和希特勒吸毒的結束。
當然,納粹並不是唯一吸毒的人。 盟軍轟炸機飛行員還被給予安非他明,以讓他們在長途飛行中保持清醒和集中註意力,並且盟軍有自己的藥物選擇 - 苯丙胺.
勞里埃軍事歷史檔案館 安大略加拿大的記錄表明,士兵應每五至六小時攝入 5 毫克至 20 毫克的硫酸苯丙胺,據估計,二戰期間盟軍消耗了 72 萬粒安非他明藥片。 據稱,傘兵在諾曼底登陸期間使用了它,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 1943 年入侵塔拉瓦時也依靠它。
那麼,為什麼歷史學家迄今為止只以軼事的形式描述毒品呢?
“我認為很多人不了解藥物的威力有多大,”奧勒反思道。 “現在情況可能會改變。 我不是第一個寫這些的人,但我認為這本書的成功意味著……未來的書籍和電影,比如 倒台 可能會更加關注希特勒猖獗的虐待行為。”
在德國烏爾姆大學任教的德國醫學歷史學家彼得·施泰因坎普博士認為,現在這一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大多數相關方都已經去世”。
“1981 年的德國 U 型潛艇電影《Das Boot》上映時,描繪了 U 型潛艇船長喝得酩酊大醉的場景。 這引起了許多希望被描繪成乾淨整潔的退伍軍人的憤怒,”他說。 “但現在大多數參加過二戰的人都已不在我們身邊,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藥物濫用的故事,不僅來自二戰,還來自伊拉克和越南。”
 |
當然,毒品的使用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公元前 1200 年,秘魯的前印加查文祭司給他們的臣民服用精神活性藥物以獲得精神活性。功率 在他們之上,而羅馬人則耕種 鴉片,馬可·奧勒留皇帝對此聞名 上癮.
維京人“狂戰士”,以“熊大衣在古斯堪的納維亞語中,著名的是在一種恍惚的狀態下進行戰鬥,這可能是服用木耳“神奇”蘑菇和沼澤桃金孃的結果。 冰島歷史學家和詩人斯諾里·斯圖魯森(Snorri Stuluson,公元 1179 年至 1241 年)形容他們“像狗或狼一樣瘋狂,咬住他們的盾牌,像熊或野牛一樣強壯”。
最近,理查德·勒茲曼 (Richard Lertzman) 和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irnes) 所著的《感覺古德博士:通過治療和給包括肯尼迪總統、瑪麗蓮·夢露和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在內的名人等名人服用藥物而影響歷史的醫生的故事》一書聲稱,美國 約翰·F·肯尼迪總統吸毒情況 期間差點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期兩天的峰會1961 年與蘇聯領導人尼基塔·克魯舍爾 (Nikita Krushcher) 會面。
越南戰爭
波蘭作家盧卡斯·卡緬斯基(Lukasz Kamienski)在其著作《射擊》中描述了越南戰爭期間,美軍如何通過速度、類固醇和止痛藥來“幫助他們應對長期戰鬥”。
眾議院犯罪問題特別委員會 1971 年的一份報告發現,1966 年至 1969 年間,武裝部隊使用了 225億 興奮藥。
“軍隊使用興奮劑助長了吸毒習慣的蔓延,有時甚至會帶來悲慘的後果,因為正如許多退伍軍人聲稱的那樣,安非他明會增加攻擊性和警覺性。 有些人記得,當速度的影響逐漸消失時,他們非常惱火,想射殺‘街上的孩子’,”卡緬斯基 2016 年 XNUMX 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寫道。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參加過戰爭的退伍軍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 全國越戰退伍軍人調整 研究 1990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在東南亞經歷過戰鬥的男性士兵中,有15.2%和女性士兵中有8.5%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根據一項研究 JAMA精神病學是一份面向精神病學、心理健康、行為科學及相關領域的臨床醫生、學者和研究科學家的國際同行評審期刊,越南戰爭結束近 200,000 年後,仍有 50 萬人仍然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其中之一是約翰·丹尼爾斯基。 他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並於 13 年至 1968 年間在越南待了 1970 個月。XNUMX 月,他為患者出版了一本自傳指南,名為《Johnny Come Crumbling Home: with PTSD》。
“我 1970 年從越南迴國,但和很多其他人一樣,我仍然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它永遠不會消失。 1968 年,當我在越南的叢林中時,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吸食大麻並服用阿片類藥物。 我們還喝了很多棕色瓶子裡的速度,”他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家中通過電話說道。
“軍隊的人在西貢和河內服用興奮劑和各種藥物,但我們在那裡,我們只是喝速度。 它裝在一個棕色瓶子裡。 我知道這會讓人們變得焦躁不安,他們會熬夜好幾天。”
“當然,有些人在那裡做了一些瘋狂的事情。 肯定和藥物有關係。 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當這些人從越南迴來時,他們在飛機上心髒病發作並死亡。 他們會陷入這樣的戒斷狀態——如果沒有藥物,飛行時間將長達 13 個小時。 想像一下在越南打仗,然後回家並在回家的路上死去,”丹尼爾斯基說。
“安非他明會增加你的心率,讓你的心臟爆炸,”他解釋道。
卡緬斯基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寫道:“越南被稱為第一次藥物戰爭,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軍事人員對精神活性物質的消費水平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當我們回來時,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支持,”丹尼爾斯基解釋道。 “每個人都討厭我們。 人們指責我們是嬰兒殺手。 退伍軍人服務一團糟。 沒有成癮諮詢。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回來後就自殺了。 多於 70,000 自越戰以來,退伍軍人已經自殺了, 58,000 死於戰爭。 他們沒有紀念牆。”
“毒品和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之間有聯繫嗎?” 他問。 “當然,但對我來說,最困難的部分是當我回來時我也感受到了孤立。 沒人關心。 我剛剛成為一名海洛因成癮者和酒鬼,直到 1998 年才開始康復。現在服務有所改善,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軍人仍在自殺——他們的自殺率更高。”
敘利亞戰爭
最近,在中東沖突中,苯丙胺(Captagon)的使用有所增加,這種苯丙胺據稱正在助長敘利亞內戰。 去年11月,土耳其官員在敘利亞-土耳其邊境查獲了XNUMX萬粒藥丸,而今年XNUMX月 1.5萬元 在科威特被查獲。 在 BBC 一部名為《敘利亞戰爭》的紀錄片中 藥物 自 2015 年 XNUMX 月起,一位用戶說道:“服用 Captagon 後,我不再感到恐懼。 你無法入睡或閉上眼睛,別想了。”
拉姆齊·哈達德 (Ramzi Haddad) 是黎巴嫩精神病學家,也是一家名為 Skoun 的成癮中心的聯合創始人。 他解釋說,Captagon“是敘利亞製造的”,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超過 40 年”。
“我已經看到了這種藥物對人們的影響。 在這裡,它在充滿敘利亞難民的難民營中越來越受歡迎。 人們可以花幾美元從毒販那裡購買它,因此它比可卡因或搖頭丸便宜得多,”哈達德說。 “從短期來看,它會讓人們感到欣快、無所畏懼,讓他們睡得更少——非常適合戰時作戰,但從長遠來看,它會帶來精神病、偏執和心血管副作用。”
卡爾文·詹姆斯 (Calvin James) 是一位愛爾蘭人,曾在敘利亞擔任醫生多年庫爾德紅新月會成員表示,雖然他沒有接觸過這種藥物,但他聽說這種藥物在伊拉克伊斯蘭國和黎凡特組織(即“伊斯蘭國”或“伊斯蘭國”)的戰士中很受歡迎。
“從人們的舉止就能看出來。 有一次,我們遇到一名 ISIS 成員,他帶著五個孩子坐在一輛運載車上,他受了重傷。 他似乎根本沒有註意到,並向我要了一些水,他非常興奮,”詹姆斯說。 “另一個人試圖引爆自己,但沒有成功,他還活著。 再說一次,他似乎並沒有太注意到疼痛。 他和其他人一樣在醫院接受治療。”
愛爾蘭成癮問題委員兼心理治療師格里·希基 (Gerry Hickey) 對最近的發現並不感到驚訝。
“妄想是課程的一部分,阿片類藥物非常容易上癮,因為它們讓人感到平靜,並給他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因此,當然,它們非常適合步兵、海軍上尉以及最近的恐怖分子,”他說。
“內閣喜歡在戰時麻醉他們的軍隊,以便殺人的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他們自己吸毒是為了控制他們浮誇的自戀、狂妄和妄想。”
“如果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渾身被麻醉,我不會感到驚訝,”他補充道。
“毒品的問題在於,人們不僅會在一段時間後失去理智,長期吸毒後身體健康也會惡化,尤其是吸毒者到了 40 多歲時。”
他解釋說,如果希特勒在戰爭的最後幾周處於撤退狀態,那麼他感到顫抖和寒冷也就不足為奇了。 “戒斷的人會陷入巨大的震驚之中,常常會死亡。 那時他們需要服用其他藥物。 需要三週的調整時間。”
“當人們問‘我想知道他們從哪裡獲得能量’時,我總是有點懷疑,”他反思道。 “好吧,別再看了。”
文章最初發現於半島電視台: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6/10/history-war-drugs-vikings-nazis-161005101505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