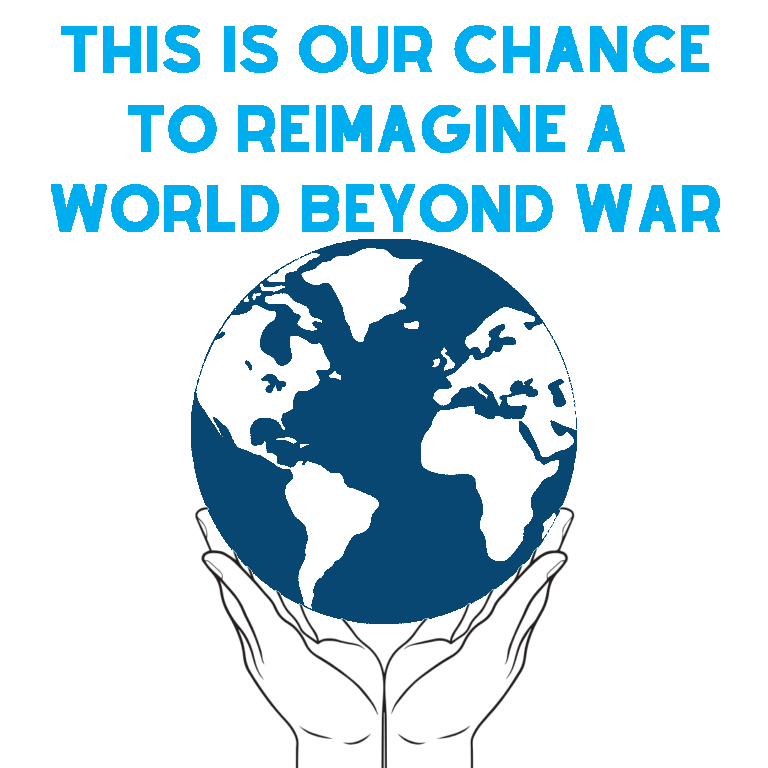作者:David Swanson,March 1,2019
顯然我們很多人都是兩者。 我對帝國或戰爭的使用率為零。 但我使用這些標籤作為兩個團體的簡寫,這兩個團體在宣傳工作中有時團結,有時不團結。
人們反對帝國和戰爭,強調帝國,傾向於避免提倡非暴力,很少談論不通過戰爭解決衝突的替代手段,通常喜歡“革命”一詞,有時提倡暴力革命或通過任何可用或“必要”的手段進行革命。
另一種則反對戰爭和帝國,強調戰爭,提倡非暴力行動主義、裁軍、取代戰爭的新結構等工具,並且沒有提及武裝防禦的“權利”或在暴力和“無所事事”之間的所謂選擇。
至關重要的是,這兩個重疊、融合併包含無限變化的群體能夠相互對話。 兩人都明白分裂的弱點。 雙方都認為跟隨對方的領導也存在很大的弱點。 所以,有時有合作,有時沒有。 但即使存在,也是膚淺的。 對話很少深入到足以找到互惠互利的策略或說服一種立場轉向另一種立場的人。
討論通常看起來像這樣:
答:學者們所做的研究似乎清楚地表明,當推翻壓迫的運動是非暴力的時,其成功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多,而且這些成功的持續時間要長得多。 即使知道暴力不太可能成功,是否仍有理由提倡或接受暴力作為可行的選擇?
B:嗯,但是什麼才算是成功呢? 而且我並不是提倡暴力。 我只是避免向受壓迫的人們發號施令。 我不會拒絕支持他們反對帝國的鬥爭,除非這符合我的策略。 我們的職責不是對人們發號施令,而是支持他們。 我永遠不會因為一個被錯誤定罪的政治犯主張暴力而不支持他的自由。
A:但是你看過這項研究嗎? 您可以從 Erica Chenoweth 和 Maria Stephan 的書開始。 您想要一份副本嗎? 你真的認為那些算作成功的例子有什麼不成功的地方嗎? 我從來沒有做過,甚至夢想過做任何事情,比如向遠處的一群人命令他們必須做什麼。 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做這樣的事情的能力非常有限,但必須承認,在與此非常相似的討論之前,我從未想到過這個想法。 我支持將所有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首先是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 我反對任何地方的一切國內外的壓迫,無論人們如何反對。 但如果有人尋求我的建議,我會向他們指出我對事實的最佳理解——誠然,這可能是錯誤的。 這種理解表明,暴力更有可能失敗,而其正義性與失敗的可能性無關。
B:但這是一個建立全球團結來打擊國際資本主義海盜的問題,如果不尊重那些受到影響並努力擺脫我們的稅款資助的犯罪的人們本身,我們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堅持要求他們按照我們的建議行事,我們就無法尊重他們,也不能讓他們尊重我們。 伊拉克人沒有反擊的權利嗎? 難道這樣的反擊就不能取得勝利嗎?
答:我們絕對沒有資格對我們的稅收和我們自己的政治失敗的受害者發號施令。 你和我在這一點上的看法非常一致。 但是,這裡有一個棘手的部分:作為人類,我們絕對有責任保衛那些在與崇高事業相關的努力中被不必要地、可能適得其反地殺害、受傷、遭受創傷和無家可歸的人的生命。 實際上,我們必須選擇站在受害者(所有受害者)一邊,還是站在劊子手一邊。 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結束了奴隸制和農奴制,但沒有像美國 1860 年代那樣經歷過暴力,而且至今尚未恢復元氣。 你很難找到比結束奴隸制更崇高的事業,但今天有很多崇高的事業等待著人們去實現。 如果美國人民決定結束大規模監禁怎麼辦? 我們是否想首先選擇一些領域並互相殘殺數百萬人,然後通過一項結束大規模監禁的法律? 或者我們想直接通過法律嗎? 難道就不能以比過去更好的方式做事嗎?
B:那麼,伊拉克人沒有反擊的權利,因為你更清楚?
答:我對權利或缺乏權利的概念沒有多大用處。 當然,他們可以有反擊的權利,有躺下什麼也不做的權利,還有吃指甲的權利。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會建議做任何這些事情。 我當然——我不知道如何說清楚,但我會一直這麼說——不會指示他們、命令他們或向他們發號施令。 如果他們有什麼所謂的權利的話,那就是無視我的地獄般的權利! 但這如何阻止我們成為盟友和朋友呢? 你和我不是盟友和朋友嗎? 我在美國軍隊佔領的國家裡有一些朋友,他們和我一樣致力於非暴力抵抗。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比我更多地支持或歡呼塔利班、伊斯蘭國或其他各種團體的行動。
B:這些並不是唯一使用或可能使用暴力的群體。 有些人被迫使用暴力,就像你被困在黑暗的小巷裡一樣。
答:你知道,我曾與在西點軍校教授“道德”的那個人辯論過,他使用完全相同的黑暗巷子套路來為帝國主義戰爭辯護。 但建造並部署巨大的死亡機器實際上與黑暗小巷中的孤獨者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一個無論其價值如何,擁有比我們想像的更多選擇的人。 組織軍事抵抗帝國的入侵或占領也與一個孤獨的人在黑暗的小巷裡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這裡的選擇確實很多。 非暴力策略的種類繁多。 當然,暴力可以取得成功,甚至是重大成功,但非暴力行動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一路上造成的損害較小,參與人數較多,未來更加團結,成功也更加持久。
B:但如果人們實際上組織起來進行暴力革命,選擇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答:為什麼呢? 難道我們不能同意反對他們反對的事情,同時又不同意他們反對的方式嗎? 我想我可能知道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的一個原因。 這是一個表明你我之間存在更深層次分歧的原因,但我認為我們只有談論它才能解決它。 就是這個。 當我要求你們在華盛頓特區、紐約或倫敦的抗議行動中公開承諾非暴力時,毫無疑問需要尊重我們遠方兄弟姐妹中某些遙遠群體對暴力的偏好。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處理的您的偏好。 你們仍然不願意致力於非暴力,儘管它可以使我們的運動規模更大,更有效地傳達我們的信息,並阻止警察滲透者和破壞者。 有時你在這一點上同意我的觀點,但通常不同意。
B:嗯,也許我們可以在其中一些觀點上達成更多共識,我不知道。 但同樣的問題確實出現了:此時此地,我們的盟友想要使用暴力; 關於什麼才算暴力也存在爭議。 我們不能通過排除人來發起運動。
A:你感覺怎麼樣? 動靜在哪兒? 當然,你也可以問我同樣的問題。 但我有一個有大量證據支持的理論,即增加擴大運動規模的機會的一種方法是公開承諾非暴力,至少在我們自己在野獸之腹的行動中如此。 我們不能通過排除絕大多數不想參與暴力的人來發起一場運動。 是的,他們可能喜歡暴力電影和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的暴力行為。 他們可能容忍暴力的監獄、暴力的學校、暴力的好萊塢選角辦公室和暴力的警察。 但他們不希望自己周圍發生任何暴力行為。
B:所以你想要一場偽君子運動?
答:是的,還有膽小鬼、小偷、吹牛者、騙子、變態、失敗者、狂熱分子、自戀者和隱士,還有勇敢的領導者和天才。 但當我們試圖引進所有人時,我們不能過於挑剔。 我們可以盡我們所知,盡力鼓勵和激發人們最好的一面,並希望他們也為我們做同樣的事情。
B:我看得出來。 但你仍然想排除持槍的人。
答:但這只是因為槍最終排除了更多的人。
乙:是啊,你也這麼說過。
一個OK。 好吧,讓我試著說一件事關於槍支。 我認為帝國有一種壓迫遙遠人民的方式,這種方式與製裁、炸彈、導彈或敢死隊不太一樣。 這是產品的提供。 美洲原住民得到了患病的毯子,但也得到了酒精。 中國人得到了鴉片。 你知道今天富裕的施虐國家給了哪些貧窮的受虐國家嗎? 槍。 地球上那些我們被訓練認為是暴力製造的地方幾乎沒有製造武器。 這些武器是從北方運來的,大部分是從西方運來的,比如一卡車的病毯子。 槍支大多殺死了居住在他們被送往的國家的人們。 我認為慶祝槍支作為抵抗手段是錯誤的。
B:嗯,這是看待問題的一種方式。 但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一些人卻不這麼看。 您在安全、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裡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們不這麼看。 你知道我們應該做什麼嗎? 我們應該召開一次會議,一次大會,不是一場競賽,不是一場辯論,而是對這些分歧進行討論,進行禮貌、文明的討論,以便我們能夠弄清楚哪些方面可以達成一致,哪些方面不能達成一致。 你認為我們能就此達成一致嗎?
答:當然。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
B:當然,你必須參與其中。 在某些方面你確實做得很出色。
答:當然還有你。 你真的活在其中。